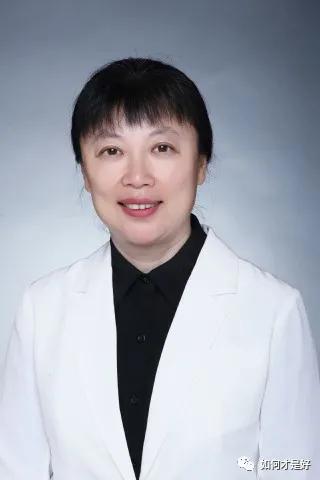
刘静芳
[作者简介]刘静芳(1967—),女,河北沧州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原题:老子之道: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中国哲学之“道”的源头审视
来源:《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摘要]“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从“道路”之“道”到万事万物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老子之“道”是一个关键环节。就《老子》第一章来看,老子之“道”处于由“具体”而“抽象”的过渡阶段,它已不是具体的“道路”,但仍未摆脱“路”的意象,其确切所指应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这一论断建立在对《老子》第一章的如下新理解之上:第一,“有”与“无”是指示事物不同状态或属性的两个“常名”,是揭示“常道”的概念工具,与“常道”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所以不能把“常道”理解为“有”或“无”;第二,“玄之又玄”的“玄”,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动词,而是名词,是“有”“无”二者的统称。第三,“玄之又玄”的含义是“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对老子之道及《老子》第一章的上述新理解,会使《老子》研究中的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关键词]老子之道;常道;常名;玄;玄之又玄;《老子》第一章
理解中国哲学之“道”是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维度,而对中国哲学之“道”的把握,不能绕开老子之“道”。老子之“道”究竟何指?有人认为它是无,有人认为它是有;有人认为它是客观实有,有人认为它是主观境界;有人认为它是价值世界的形上基础,有人认为它是客观世界的总根源、总根据[1]。要想在众说纷纭中把握老子之“道”的确切内涵,须回到对《老子》第一章的审慎的解读。
一、对老子之道的新理解:方法与结论对老子之道的把握,离不开对《老子》第一章的阐释,而对《老子》第一章的不同阐释,与不同的方法论选择有关。就方法论而言,对《老子》第一章及老子之道的理解,应重视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契合大的时代背景来理解《老子》第一章及老子之道。这种契合至少有两方面的要求:首先,不可过高估计老子之“道”的抽象性。大体而言,《老子》在中国哲学之“道”的理论提升方面,表现出一种较早的自觉。这一方面意味着老子之道的出发点,更多地应是“道”的最普通、最常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作为“道”的提升结果的“常道”,与“道”之“道路”本义,仍可能存在意象的关联。其次,不应低估《老子》的智慧和思维水平。冯友兰认为,《老子》的思辨能力是很高的[2](P290)。如果我们承认先秦时期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已达到了较高的逻辑思维水平,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合理地推定,在正常情况下,《老子》的思维合乎基本的逻辑要求。
第二,注重从义理贯通的角度去理解《老子》第一章及老子之道。如果我们肯定《老子》的思维合乎基本的逻辑要求,那么就应承认其义理是贯通的。相应地,《老子》第一章作为一个涉及核心概念的重要章节,其逻辑和义理应该经得起推敲。基于这种认知,我们应坚持如下两个原则:首先,在不同文本、不同解释发生冲突时,要以义理的贯通作为重要依据。其次,在批评《老子》第一章逻辑不清、文意不明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第三,以一种“去蔽”的自觉,理解《老子》第一章及老子之道。《老子》的传播既久且广,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诸多诠释版本。对于这些诠释版本,既要肯定其思想生发的积极意义,更要注意区分《老子》的思想与后人对《老子》思想的解释。换言之,在涉及老子思想“本身”时,我们应有一种“去蔽”的自觉,即对后来附加于其上的东西保持必要的警惕———不仅要警惕“反向格义”的影响,也要警惕后来的各种解释(包括早期解释)所生发的各种影响。
基于上述方法论原则,在吸纳前辈及时贤诸多洞见的基础上,本文强调以下几点:第一,老子之道(“常道”),既不是后世所理解的“无”,也不是后世所理解的“有”,而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第二,“有”与“无”是两个“常名”,是阐释“常道”的概念工具,它们与“道”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第三,“玄之又玄”之“玄”,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动词,而是名词,是有、无二者的统称。“玄之又玄”的含义应是从这一“玄”到那一“玄”,即“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
上述论断的得出,基于对《老子》第一章的如下断句(①人们对《老子》第一章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这些分歧既表现在断句、文本上,也表现在逻辑、义理上,本文对不同理解的取舍,以义理的贯通作为重要原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以这种断句为基础,我们尝试对其作这样一种理解:
可以行走的“道”,不是“常道”。可以名状别物的“名”,不是“常名”。“无”这个名,用来指称天地之始;“有”这个名,用来指称万物之母。“无”和“有”这两个名,不是通常用来“名状别物”的名,而是常名。使用常名“无”,是为了考察道之微妙的一面;使用常名“有”,是为了考察道之昭明的一面。“无”和“有”,来源相同而名称不同,它们都可以称为“玄”。从这一“玄”到那一“玄”(或者说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不是两地之间可以行走的具体道路,然而是一切变化的门径,这种一切变化均须遵循的门径,即“常道”。
二、对老子之道的新理解的理由面对人们对《老子》第一章及老子之道的诸多解释,上述新理解,只能说是一种假说。对于这一假说,我们针对既有理解中的重要分歧,逐句提出一些辩护的理由。
“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行走的“道”,不是“常道”。
在对这一句的理解上,最值得注意的分歧是对“道可道”的两种理解——其一,将其理解为可以言说的道理;其二,将其理解为可行之路。其中,较为通行的是第一种,本文采取第二种理解。但对于第二种理解中的“行”,仍可以有多种解释,如行走、践行、遵行等等。本文采用其最具体的含义———“行走”。这样一来,“道可道”中的第一个“道”,是路的意思,第二个“道”,是行走的意思,“道可道”就是可以行走于其上的道路的意思。这种理解,比起将“道可道”解释为“可由之道”“可从之道”“可践行之道”来说,是一种更为具体和原初的理解。
之所以把“道可道”理解为“可以行走于其上的道路”,是因为《老子》在这里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使“常道”与人们惯常所理解的“道”形成一种对比,进而阐释“常道”之不同。这样一种出发点,决定了“道可道”中,无论是作为名词的第一个“道”,还是作为动词的第二个“道”,都应是其本义或最普通的意义。而名词“道”的本义是路,相应地,动词“道”的本义是走路。而“道可道”,也就是可以行走的具体道路。尽管在先秦时期,“天道”“人道”中的“道”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远离“道”的本义,但无论如何,老子是第一个对“道”这一概念作自觉抽象的人。这种抽象的起点,理应是“道”的最原初、最普通的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不赞同把“道可道”理解为可以言说的道理,因为“道”的“言说”义,并不是其最原初的意义。庞朴认为,道的原始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道的第一重引申义是“引导”,言说或谈说之义,可能已经是道的第二重引申了[3]。人们之所以多采用“道”的“言说”一义,一方面可能是受到了后来的解释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了“名可名”的影响。如果是受到了“名可名”的影响,那么解释者很有可能把“道可道,非常道”与“名可名,非常名”两句话放在了同一层次上。但是,我们后面的分析将表明,“名可名,非常名”是对“道可道,非常道”的一种转折,而不是对其内涵的相近表达。
“道可道,非常道”中提出了“常道”概念,这表明《老子》想赋予“道”以一种新意义。这一新意义的重心是“常”,或者说是恒常。但是,《老子》不是通过另立概念的方式,而是通过给“道”加一“常”(“恒”)的限定来实现其目的,说明“常道”与“路”仍有关联———它不是从甲地到乙地的具体的路径,也不是人们可以“踩踏”于其上的路径,但它仍有可能是某种“路径”,而且这种路径还带有一种恒常性。
“道可道,非常道”既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常道”,那么,行文的合理推进,理应是紧接着对作为新概念的“常道”进行说明。但“道可道,非常道”的下一句,却是“名可名,非常名”。这两句尽管结构相同,但后一句并不是对前一句句意的强调或重复,而是对前一句的转折。这种转折的目的何在?在于借助“常名”来阐释“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可以名状别物的名,不是“常名”。
对“名可名,非常名”一句的理解,最大的问题出在“常名”上。有人认为“常名”是“道”之名,有人认为“常名”是“无名”。但在《老子》第一章中,这类理解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文义上,都不顺畅。蒋锡昌认为,“常名”是《老子》一书中所用之名,老子提出“常名”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其所用之名与普通意义上的名有所不同[4](P165)。但是,这样一种理解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人们仍会追问,“常名”与普通意义上的名究竟有什么不同?
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此句中的“名可名”之“名”。基于理解“道可道”之“道”的思路,对于“名可名”之“名”,我们也应从其最普通的意义入手。“名可名”中的第一个“名”是名词,第二个“名”是动词。作为名词的“名”,最普通的意义是名称、名字。作为动词的“名”,最普通的意义是“命名”。一般情况下,名称或命名的意义何在呢?《说文解字》认为:“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表明,名的功能是使被命名的对象在昏暗中明晰起来。刘熙在《释名·释言语》中把这一层意思说得更明白,“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而王弼把“名”与“形”相联系,或许也是有见于此。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之所以为“人”命名,称其为张三、李四等,主要目的是为了区别“不同”的人;之所以为“物”命名,称其为山川、河流等,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对其进行摹状区分。这意味着,普通意义上的“名”,其主要作用是“名状别物”。既然普通意义上的名的作用主要是名状别物,那么与普通的名相区别的“常名”,就有可能指那些难以名状别物的“名”,例如“有”,例如“无”。有、无这样的“名”,在“名状别物”方面是有欠缺的,但它们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可以涵括“很多”事物或状况。例如“有”这一名称,虽不能区分张三、李四、山川、河流,但张三、李四、山川、河流都可以被囊括于“有”,就此而言,“有”是一个“恒常”的名。
明了了“常名”与普通的“名”的区别,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追问,在老子心目中,究竟哪些名属于常名?这些“常名”所指的对象是什么?老子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这个名,用来指称天地之始;“有”这个名,用来指称万物之母。
在这一句的理解上,最明显的分歧在于断句。当然,断句不同,理解也会有所不同。这一句主要有两种断句方式:第一种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二种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本文采用的是第二种断句。第二种断句遇到的一个重要反驳,是其出现得较晚。但笔者认为,出现得早的理解以及与其相应的断句,并不能确保其合乎《老子》的原意。第二种断句遇到的另一个反驳是,“无名”作为《老子》的重要概念,是一个专名。但是,仅就《老子》文本本身来看,“无名”是一个专名的证据并不充分。把《老子》中出现的“无名”,如“道常无名”“道隐无名”中的“无名”,拆解开来理解为“无”与“名”,并不会产生义理不通的问题。
以有、无断句的主要理由是,“道”“有”“无”是《老子》的核心概念,而《老子》第一章是集中阐释这三个概念及其关系的章节,这就意味着,“有”与“无”在《老子》第一章中应有所界定。如果以无名、有名断句,并且认为“无名”“有名”各自不可分割,那么这一章就没有直接揭示有、无所指的句子,这不符合该章的主旨。而以有、无断句,既符合第一章的主旨,也与《老子》的整体思想相契合,更重要的是,这与上文提出的“常名”问题相契合。《老子》既然提出了“常名”,那么原则上就要对“常名”(“恒名”)有所阐释,而通行的对《老子》第一章的解释,多对“常名”不予深究,恐未合《老子》原意。以有、无断句,意味着“有”与“无”是“名”,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有”与“无”是普通意义上的名还是“常名”?按照前文对名与常名的区分,以及行文的自然逻辑,“有”与“无”这两个名,理应是常名。但究竟二者是不是常名,还要进一步看有、无这两个名的所指。《老子》认为,“无”这个名,是指天地之始;“有”这个名,是指万物之母。从有、无的所指来看,可以进一步确证本文之前的推断,那就是,有和无,应是两个常名。常名与普通意义上的名的区别在于,它很难名状别物。由于“无”所指的“天地之始”是不可名状的,所以“无”不是普通的名,只能是常名;由于“有”所指的“万物之母”也不是可以进行区分的,所以“有”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名,只能是常名。
以上分析表明,以有、无断句,进而把有、无看成是两个常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里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常名难以名状别物,那么《老子》为什么还要设立有、无这样的常名呢?接下来一句,《老子》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无”和“有”这两个名,不是通常用来名状别物的名,而是常名。使用常名“无”,是为了考察道之微妙的一面;使用常名“有”,是为了考察道之昭明的一面。
这一句主要有两种断句。第一种断句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第二种断句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本文采用第二种断句。第二种断句遇到的一个重要反驳是,它缺少出土文献以及早期理解的支持。但对于早期文本和早期理解,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定,一个文本的出现与该文本的流传、解释之间,其时间间隔越短,理解歧出的可能性就越小。但可能性小不等于没有可能。如果同时代人的相互理解都可能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确定无疑地认为,早期出现的版本或理解一定是正本或正解。廖名春认为,当文本与《老子》的内在逻辑发生矛盾时,应优先考虑《老子》的内在逻辑[5]。
按照《老子》第一章的内在逻辑,如果前面讨论的是常名问题,那么这里通常也应是对这一问题的引申。这样一来,有欲、无欲的断句和解释就可能是一种歧出。如果我们仍一贯地考察常名的问题,那么这一句顺理成章的解释应是:使用常名“无”,是为了考察道之微妙的一面;使用常名“有”,是为了考察道之昭明的一面。这样一种理解,不仅在逻辑上与上文提出“有”“无”两个常名相连贯,而且在下文中,“此两者”也不会产生所指究竟为何的问题。
确定了有和无是两个常名,并且这两个常名的作用是指称对象的不同方面,我们对对象(“常道”)的把握仍不够全面——只是知道其有微妙和昭明的两面,但对象(“常道”)与这两面的关系仍不清楚。所以,《老子》接下来继续借助有、无这两个常名,为对对象(“常道”)的最终阐释作铺垫:“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无”和“有”,来源相同而名称不同,故二者均可称之为“玄”。
在对这一句的理解上,主要分歧在于对“此两者”以及对于“玄”的不同理解。首先,“此两者”的所指,有人认为是有与无,有人认为是有名、无名,有人认为是有欲、无欲,有人认为是始与母,有人认为是妙与徼,等等。本文认为,“此两者”从上下文来看,当指作为常名的有与无。这可从“同出而异名”得到一定的确证。其次,对于“同谓之玄”的“玄”,人们多侧重于从其内涵———幽暗、幽深、混沌不分、不可分别等的角度去理解,在这种理解之下,“玄”极易被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但本文认为,这里的“玄”主要是名词的用法,它是一个命名,一个名称。庞朴认为,“玄”的本义应是水的漩涡,漩涡的微妙之处在于其回旋,在于其“本应该有,但必须不有”[6](P129)这样的“玄”是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的,是有与无的统称。事实上,《老子》中的“玄”,如“玄德”“玄同”等的“玄”,都可以理解为有与无的统称(①详见另文。)。
把“玄”这一名称加之于有、无,说“有”与“无”是“玄”,意欲何为?本文认为,首先,这是对有、无的“常名”性质的进一步肯定。常名的特点是难以名状别物,而玄也有不可分别、幽暗、混沌的意思,所以把有、无称为玄,合乎有、无作为“常名”之属性。其次,这是为说明“常道”所作的一个铺垫。常道是什么?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从这一“玄”到那一“玄”(或者说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不是两地之间可以行走的具体道路,然而是一切变化的门径,这就是“常道”。
对这一句的理解,论者间的一个很大分歧在于对“玄”的词性的把握。有论者把“玄”看作是形容词,理解为幽深又幽深之类。也有论者把“玄”看作是动词,理解为“损之又损”。我们仍是一贯地把这里的“玄”看作是一个名词,把它看成是对有、无的一个通称。这样一来,对“玄之又玄”的最合理的解释,应是“从此玄到彼玄”。具体来说,就是“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涉及路径问题,这就与“道”的本义联系起来了。而接下去《老子》说,这是“众妙之门”,是一切变化的门径或路径,故这个众妙之门无疑就是“常道”。
到此为止,第一章最初所关注的“常道”的内涵,就借助常名“有”与常名“无”,得到了明确的揭示:“常道”是一种路径,这一路径一端连着有(常名“有”的所指),一端连着无(常名“无”的所指),是包含有与无,并且连接有与无的路径或门径,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它之所以是常“道”,是因为它仍未完全摆脱“道路”之“路径”意象。它之所以是“常”道,是因为它不是一具体的“此地”与“彼地”之间的路径,而是“有”与“无”之间的路径;它不是可感触、可踩踏的路径,而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路径。它是“恒常”的路径,是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不得不经由的路径,因为一切事物的变化无一不是“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
三、新理解对有争议问题的尝试性解答对《老子》第一章及老子之道的新理解,尽管有一些根据,但总体而言,仍是一种假说。关于这一假说的合理性,还需要其解释力的支持。下面,基于对《老子》第一章及老子之道的新理解,对《老子》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一些尝试性的解答。
问题一,《老子》第一章,是否有一个明晰的逻辑结构?论者对《老子》第一章众说纷纭的理解本身,表明人们对此是持不同意见的。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老子》第一章有一个明晰的逻辑结构:《老子》第一章开篇就以作为“路”的“道”为参照,提出了“常道”问题。之后,它并未直接界定何为“常道”,而是进行了一个转折——去寻找阐释“常道”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常名”。提出“常名”概念后,《老子》转而界定了有、无两个概念,这并不突兀,因为“有”和“无”正是用来揭示“常道”的两个“常名”。在规定了有、无两个常名的所指,指明了这两个常名的不同功用之后,《老子》把有和无通称为“玄”,以两“玄”互动所形成的路径,来揭示本章最初提到的“常道”的内涵。综上所述,《老子》第一章的总体结构可以表示为:常道—常名—有、无两个常名—有(玄)、无(玄)的互动路径—常道。
问题二,《老子》第一章的核心概念是否是清晰的?以往人们之所以不断重新诠释《老子》第一章,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这种分歧,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老子》第一章中的概念不够清晰。本文认为,如果基于最普通的意义去理解“道”与“名”,那么《老子》第一章所涉及的重要概念及这些概念间的关系,都是比较明晰的:“常名”,指难以名状别物之名;作为常名的无,指天地之始;作为常名的有,指万物之母;“玄”是有、无两个常名的通称;“道”是可以踩踏于其上的具体道路;“常道”是有无(所指)之间周行的路径。
问题三,老子之道与有、无是什么关系?基于本文的理解,首先,道不是无。无指“天地之始”,只是道的一个方面。其次,道也不是有。有指“万物之母”,也只是道的一个方面。道不是无,也不是有,而是有、无的统一。“道统有无”,是很多论者所持的观点。至于道如何统有、无,很多论者却语焉不详。张岱年认为:“有与无皆谓之玄,玄之又玄即道,有无同出于道。道一方面是无,一方面也是有。”[7](P245)这一论述与本文的观点接近,但其细节仍不够明晰。而要对老子之“道”获得更为确切的理解,须指明道、有、无三者结合的方式。本文认为,道是有、无(包含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关于有、无之间的“周行”,很多学者已作过探讨。施昌东、潘富恩认为,无—有—无之间是周行的,这一周行路径更具体的表述是:无—象—物—天地—万物—无。但他们并非把这一周行的路径本身看成“道”,而是把道等同于无[8]。王博认为,“道的循环运动其实就是从无物到有物,再由有物复归到无物的过程”[9]。他形象地将这一循环运动用一个两极分别为“有(惚)”和“无(恍)”的圆圈来表示。王博基于对“恍”与“惚”的独到分析得出了上述结论,而本文对《老子》第一章的新理解,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
问题四,为什么对“不可言说”的“道”,《老子》有诸多言说?本文的回答是,这一困惑的产生,源于对“道可道,非常道”的这样一种理解:“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10](P77)但如果将其理解为“可以行走的‘道’,不是‘常道’”,上述困惑的重要预设就被抽掉了。按照本文的理解,“道”之不可言说,并不是《老子》的强主张。结合《老子》其他章节,我们至多只能承认,普通意义上的名,在把握“道”时有其局限性。但《老子》通过对“常名”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名”与“道”的紧张。
问题五,为什么《老子》提出“常名”后,未进一步分析、阐释它?曹峰认为,在《老子》研究史上,人们似乎从未重视过“常名”问题,“查阅古典文献,也完全不见‘常名’或‘恒名’的用例”[11]。那么,老子是否在提出“常名”后,就置而不论了?按照本文对《老子》第一章的理解,《老子》在第一章中提出“常名”后,并未转移论题而将其搁置。相反,在第一章中,只有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直接讨论“常道”———第一句提出常道问题,最后一句回答常道是什么。除了这两句,《老子》第一章所讨论的都是“常名”(有、无)问题。当然,《老子》的其他章节并未出现“常名”字样,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章节未涉及“常名”问题。根据《老子》第一章对“常名”(难以名状别物之名)的理解,老子所说的常名应该不限于“有”与“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老子·第十四章》)中的“夷”“希”“微”从难以名状别物的角度看,都可以说是常名。
问题六,如何看待《老子》第二章中“有无相生”、《老子》第四十章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郭店楚简中“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之间看似不一致的关系。按照本文的理解,“道”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在承认道的“周行”的前提下,“有无相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从道的“周行”的角度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只是强调了道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从无到有”这一面。之所以强调这一面,是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万物之“生”,如果讨论的是万物之“亡”,那么可能就会涉及大道周行的“从有到无”的一面。另外,郭店楚简《老子》甲本中,与“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相对应的文字是“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一些学者推测,这里漏了一个“有”字———原文应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另一些学者则持反对观点。然而基于本文对“周行”之道的理解,无论加不加“有”字,这一句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以有、无为两极的周行路径上,说天下之物生于有,通;说天下之物生于无,通;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通。也就是说,基于道之“周行”,上述诸种说法均成立,而且彼此之间并不构成矛盾。
问题七,如何理解“道”之“生”?《老子》第四十二章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提法。这说明,《老子》认为“道”能“生”。我们把“道”理解为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周行的路径”如何能“生”?
对道之“生”的理解,离不开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解读。在对这句话的解读上,有两种典型意见:其一是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只是抽象地说明了事物由简单到分化的程序;其二是认为一、二、三确有所指。
上述两种意见,各有其合理性,但都不够准确。老子所提出的“道生”模式,是一种新模式,这一模式中的一、二、三,确实是对事物分化的一种抽象表达。但这一模式所针对的,是一种旧模式。从其针对的旧模式来看,一、二、三隐有所指。老子的“道生”模式,所针对的是《周易》的模式。《周易》的模式是后来学者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的模式。由于是以《周易》的模式为针对物,所以老子所谓“二”,隐约对应着“阴阳”,老子所谓“三”,隐约对应着“八卦”。为什么“三”对应着“八卦”?因为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是由“三爻”构成的。“三”与八卦的对应,也可以从“三生万物”得到一定的印证。“三生万物”应指“八卦”生万物,“八卦”生万物也就是乾、坤、震、巽或者天、地、雷、风等八种要素生万物。为什么《老子》只是“隐约地”对应《周易》的模式而不是直接采用《周易》的模式?因为老子对“道”的新理解,已经与《周易》的模式发生了冲突。老子之道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其所谓道,是统有无、统阴阳的道,但在《周易》模式中,“二”所对应的“阴”与“阳”是二分的,“三”所对应的“八卦”中,“乾”是纯阳的、有阳(爻)无阴(爻)的,“坤”是纯阴的,有阴(爻)无阳(爻)的,而“统有无”的老子之道,支持的不是阴、阳的分割,而是“万物负阴而抱阳”,是“冲气以为和”。这意味着,主张“道统有无”,须放弃《周易》分割阴阳的世界生成模式,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模式,正是旧模式的替代物。
那么,新模式中的“道”如何“生”万物?老子所谓“生”,应该是“化生”[12](P331),而有、无之间的周行之道,为“化生”提供了前提性条件。首先,道为化生提供了路径。化生不可能脱离“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过程,这意味着它一定是在有无之间的周行路径上的生。没有这样的路径,就不会有“化生”。其次,道为“化生”提空了时空条件。化生离不开时空的绵延,而道的“周行而不殆”,打开了时空的维度。老子的道“大”、道“久”之说表明,道关联着时空[7](P244),而脱胎于《老子》的《中庸》之“悠远”“博厚”的宇宙生成模式[13],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老子之道的时空特征。总而言之,老子所谓“道”之“生”,是提供前提与条件之“生”。离开“道”以及道所打开的时空,“生”或者说“化生”是不可能的。
“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从“横列”的角度看,人们对中国哲学之“道”的意谓,有各种论说:有论者认为道是“精气”,有论者认为道是“万理之所稽”,有论者认为道是“共相”,有论者认为道是“本体”,有论者认为道是“总规律”,等等。但是,从“纵贯”的角度看,所有这些理解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老子之“道”。那么,这些理解与老子之道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这些对“道”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老子之道的“引申”,但这些“引申”并不等于老子之道本身。老子之道,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大道至简”。它“甚易知”“甚易行”(《老子·第七十章》),因为大道不过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只要观其复,就能择定立场,把握先机。但为什么“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过于看重“有”以至于轻视了“无”。《老子》之所以给人以重“无”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有、无之间的路径本身无形无象,另一方面是因为要阐明大道的“周行”,就必须对人们重“有”的倾向进行纠偏,因而必须不断重申“无”的重要性。但强调“无”的最终目的,是凸显“道”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而不是论证道即是“无”。老子之道,其究竟所指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这是后来诸种对“道”的理解的原初意象。意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对中国哲学之“道”的源头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由此对之后发展出来的“道”的各种意谓形成一种历史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2006(2).
[2]三松堂全集:第8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3]庞朴.解牛之解[J].学术月刊,1994(3).
[4]李若晖.老子集注汇考:第1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5]廖名春.《老子》首章新释[J].哲学研究,2011(9).
[6]庞朴文集:第1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7]张岱年全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8]施昌东,潘富恩.论老子“道”的学说[J].文史哲,1962(4).
[9]王博.老子哲学中“道”和“有”、“无”的关系试探[J].哲学研究,1991(8).
[10]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曹峰.《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北大汉简《老子》的问世为契机[J].哲学研究,2011(4).
[12]庞朴文集:第4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3]孙以楷.道家与《中庸》[J].江淮论坛,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