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易批八字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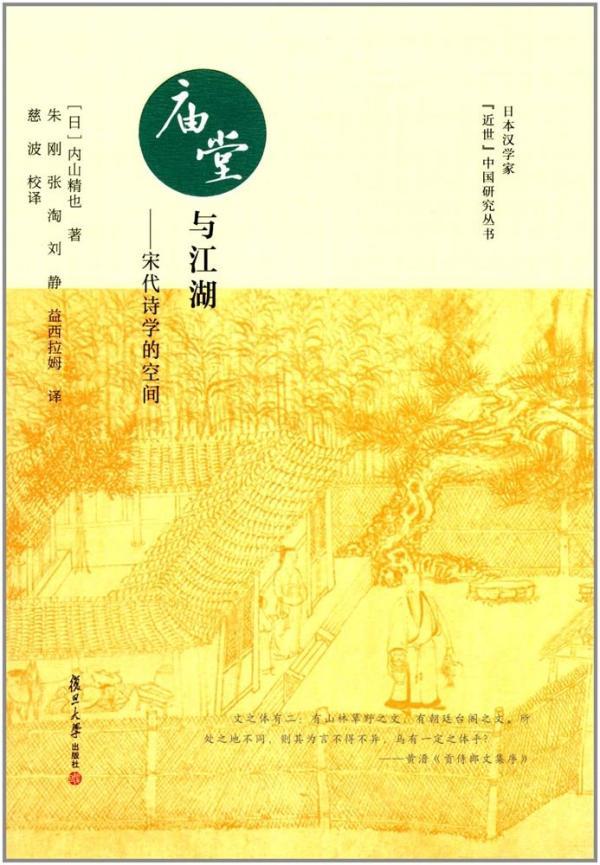
《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南方周易批八字173,[日] 内山精也著,朱刚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309页,39.00元
以赛亚·伯林尝区分两类认知方式:刺猬型与狐狸型。前者思绪集中,“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后者思绪发散,“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伯林《刺猬与狐狸》,收入《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25页)。内山精也先生的宋诗研究,近乎刺猬型。三十余年间,南方周易批八字173他的论述对象自北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家延展至南宋四灵、江湖派诗人,旨趣却一脉贯通。近来其部分论文,中译后集结成册,题为《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刊行(朱刚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下引此书仅标页码)。内山先生的学术风貌,于此足窥崖略。
书中首篇《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尤为提纲挈领之作。兹先以是为核心,旁参其他篇章,勾勒著者观念架构。
内山先生自言:力图“清理出有关‘士大夫诗人’的理想范型”(第5-6页),后文又论及“脱离南方周易批八字173了士大夫的理想范型”的四灵和江湖派(34页)。准确说来,此篇所讨论的,是某种诗人范型由士大夫向非士大夫阶层流转之迹。宋代士大夫崭露头角,始于仁宗朝,推动力在“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录取名额的增多”(第3页)。进士考科目对于政见、学养、文采皆有所要求,促使“官—学—文”三位一体型的知识人大量涌现。士大夫诗人的理想范型,即是兼具官僚、学者、诗人身份的三角结构(第7页)。官僚一端指向诗作的政治、社会维度,学者一端指向诗作的学问维度,诗人一端指向诗作的艺术维度。其中官、学两端,乃士大夫有别于普通诗人的特殊处。随着士大夫诗人群历时演变,三端迭相消长。消长之由,须从“围绕士大夫的作诗环境或者说言论环境”(31页)找寻。北宋后期党争加剧,士大夫处于高压之下,作诗不便直接表露政治、社会关怀,“官”的一角退居次位。为了“在诗歌中强调其作为士大夫的姿态”(24页),只有突显“学”的一角,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由是而出。南宋自秦桧死后,言路稍开,加以面对中原沦陷,爱国题材天然拥有政治正确性,诗歌系心时事之风、或说“官”的一角衰而复振,“学”的一角退居次位,诗风趋向“放达和明快”(26页),南宋三大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由是而出。
南宋后期,四灵与江湖诗人相继而起,除个别人物如刘克庄外,他们或沉沦下僚,或终生未仕,置身士大夫文化的边缘或界外,作风因之一变,写下许多“脱离社会、非学究式的诗篇”(33页)。“官”与“学”携手隐退,只余孤零零的“文”。必须补充一句,这并不代表诗艺上的极意求工。本书第十二篇指出:消解政治、社会关怀造成题材缩减、限于近体造成表达方式单一,都降低了门槛,使得写诗人口增长,诗作通俗化(303页)。“文”的一面,在此仅体现为一点小机智而已。
首篇所述,纲维略备,但也留有未尽之义,待后续篇章深化。就细节言,第五篇在南宋三大家中,比较陆游与杨万里,认为后者少写爱国题材,青睐缺乏学问底子的晚唐体,明诏大号,凡此种种,为四灵与江湖派导夫先路。“陆游更多地倾向于留在士大夫诗人框架之内,而杨万里身上却潜藏了从这个框架逸脱出去的倾向”(112页)。对两人诗史角色之异同,辨析更为细致。就整体言,首篇未遑揭出的,尚有一重要论题:两宋民间刻书业的迅猛发展。内山先生对此研究有素,他上一部中译论文集,题目便是《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所谓“传媒”,即指刻书业。不过上一书侧重士大夫文学,还未下移至非士大夫文学,所论不若本书全面。本书第二篇讨论苏轼两度为官杭州诗作,指出元祐时期(1089—1091)作品,常次熙宁时期(1071—1074)作品之韵,或援用后者诗语。究其原因,熙宁诗作早有坊刻本《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出售,在同时代广泛流播。苏轼可能切身体会到其影响力,故在后一任期,“自然地想起并运用起这种在他之前不存在的创作手法”(58页)。简言之,刻书业介入了士大夫诗人的创作过程。及至南宋,书商陈起编刊《江湖小集》,陆续推出江湖诗人,介入程度更深。陈氏非士人,而亲自操刀编选,并且“为了制作出畅销诗集,对著者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199页)。如果说士大夫和民间刻书业相遇,大体属于被动状态;那么非士大夫则与之更多即时互动。

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
综观上述架构,若干节点,承继之迹宛然。北宋经由科举造就新型士大夫,呼应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内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收入《东洋文化史研究》,林晓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03-111页),本书第九篇引之(215页)。南宋后期诗人的非士大夫化、平民化,呼应吉川幸次郎之说(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第六章第一节,收入《宋元明诗概说》,李庆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138页),本书第十一篇引之(280页;其余或明或暗引吉川氏论点处甚多,参看92、99-100、221、255页)。吉川氏著作,一度流行于美国汉学家间,逐渐构造出与内藤氏不同的“(南)宋元明转型”说(譬如可参看Paul Jakov Smith,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ress, 2003)。两说看似互不相下,却和谐共存于内山先生论著之中。盖因所异无非两期变化,孰为本质性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然而两期皆变化显著,却是一个事实。倘若悬搁价值判断,单考察事实,则两期变化,未尝无声气可通。即以文学创作而论,内藤湖南所揭示的中唐以降贵族性文学向庶民性文学转移态势(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110页),与吉川幸次郎所揭示的南宋文学平民化走向,便若合符契。此外,内山先生抽绎宋代士大夫理想范型,归于“官—学—文”三位一体,也早由王水照先生提出(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27页)。本书意义则在于,将这些不尽相涵的观点,融贯成一套自洽系统,用以研索诗史现象,得出不少具体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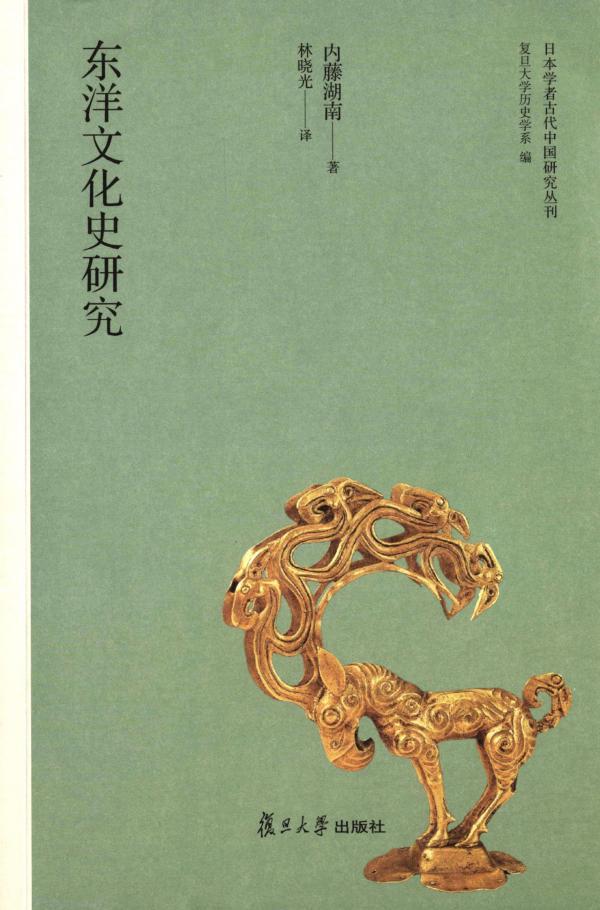
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
这套系统的轴心,乃是“理想范型”。“范型”一词,原文为“モデル”,对应“model”,也可译作“模型”。内山先生有意识运用这一工具,分析两宋诗人,方法颇引人注目。今就此作一讨论。
宋代诗人的理想范型,在士大夫与非士大夫之间移步换形。这两阶层之分,构成论说的基本前提。内山先生给“士大夫”所下定义,是“科举出身的官僚”(第6页),不包括“从事举业的书生和累举不第者”(219页注①)。他区别两个阶层,纯以中举与否为准。可是,方从事于举业者,身份虽为布衣,思维与知识的养成途径,却同中举入仕者并无二致。沟而外之,界限似乎太严。相比之下,史伟先生探讨南宋末年情形,分为科举士人与非科举士人两大阶层,思路似更合宜(史伟:《宋元之际士人阶层分化与诗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62页,“南宋末期士人阶层分化图”)。这是“士人基于谋生方式、手段上的不同而产生的阶层分化”(同上,23页)。准备赴考者别无谋生方式,也划在科举士人范围内。另谋生计者,则必然在思维与知识上重作准备。内山先生的分法,专注于研究对象的客观境遇;史伟先生则兼顾客观境遇与主观选择,视野更加立体。
说到理想范型本身,则是一抽象建构,撷取点滴现实特征,组成自身一致的系统,或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它有助于研讨与表达,但使用者要时刻注意分辨其与现实之离合,以防削足适履。内山先生构建的诗人范型,在运用得当时,确能推进对现象的认识。譬如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有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小川环树视为他萌生诗人自觉的瞬间。内山先生则指出:“陆游在剑门的发问自然是在他作为士大夫,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时生发的”,无碍于他“一生成为士大夫”的姿态(172、173页),解读更透入一层。无独有偶,钱锺书先生论这联句意,归纳两方面前代传统:一是李白、杜甫、黄庭坚居蜀而获诗艺滋养,二是李白、杜甫、贾岛、郑綮等诗家以骑驴见称,由此推阐:“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78页),着眼点也在诗人身份之自觉。后来赵齐平先生更献一解,结合陆游当时由南郑前线调任成都的背景,指出这两句诗“明明是以自南方周易批八字173我嘲弄的方式表现对内调的极大不满,悲愤痛切”(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29页),着眼点则在政治层面,与内山先生所见略同。本书取“官—学—文”三角结构考察士大夫诗人,政治、社会关怀是其一角,自然备受重视。陆游诗“好谈匡救之略”(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334页),这方面表现之突出,世所公认,又自然成为南宋士大夫诗人的典型。“此身合是诗人未”之问,若仅目为诗人的身份自觉,显然无法与上述形象切合;而一旦释为政治感慨,便即通体浃洽。这是内山先生别出新解的深层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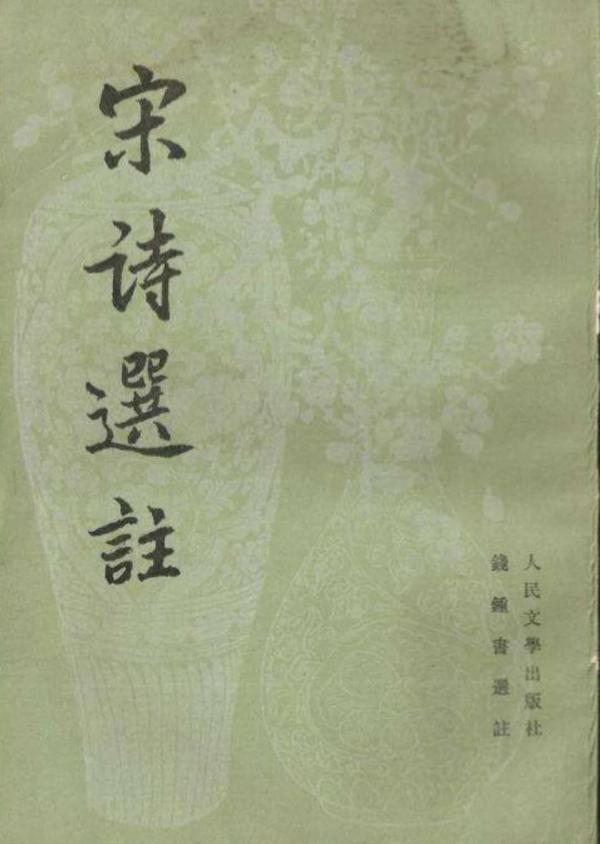
钱锺书:《宋诗选注》

钱锺书:《谈艺录》
然而另一方面,本书所提炼的理想范型,与历史现象又不无凿枘。譬如在著者看来,非士大夫诗人之作“脱离社会、非学究式”,舍弃了“官”与“文”两端。事实上,不合之例随在多有,江湖派诗人戴复古便可为证。他以布衣之身,偏多“闵时忧国之作”(马金:《书石屏诗集后》)。《论诗十绝》其五云:“陶写性情为我事,留连光景等儿嬉。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吟咏期于“有用”,心香一瓣,常在“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处(《论诗十绝》其六)。政治、社会关怀,较之士大夫诗人不稍逊色,便非内山范型所可涵盖。本书论析具体现象,也偶显此弊。譬如第五篇论南宋淮河诗,引释文珦《寄淮头家兄》,中有“故园松菊在,何必恋微官”之句。内山先生写道:“文珦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僧侣身份,担心远赴淮上的兄弟而劝他辞官归乡。若换成士大夫诗人,即便在相同的处境下,恐怕也不能写这样的诗。”(121页)非士大夫诗人的不问时事,与士大夫适成对比。然耶否耶?同篇前文引许及之使金返途作《临淮望龟山塔》:“几共浮图管送迎,今朝喜见不胜情。如何抖得红尘去,且挽清淮濯我缨。”后半用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孟子·离娄上》,又见《楚辞·渔父》)之典,流露弃官归隐意向。此为士大夫之诗,而宗旨与释文珦如出一辙。内山先生解作“因望见龟山塔……而感知淮河已近,顿时消除了紧张”(106页),反而未达一间。又如第六、七、八篇,梳理唐宋两代诗人别集演变轨迹,描述为一个自觉意识日益滋长、与民间刻书业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过程。在北宋初期,举王禹偁自编《小畜集》、杨亿“一官一集”两例,认为:“从王禹偁对集子命名时体现出的讲究(引按:“小畜”为《周易》卦名),以及杨亿一生都不断自编自撰集等行为来看,他们的主体意识比唐代诗人明显更进一步。”(145页)但是一官一集,并非杨亿首创,南朝王筠已有之。《梁书》卷三三本传载:“(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吏部佐”,胡旭《先唐别集叙录》疑为“吏部、左佐”之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61页),这一例早于唐代。杨亿之举,是否可理解成对唐人的踵事增华,恐亦难言。
归根结底,理想范型只是事物一部分特征的提取与放大,即便运用自若,也仅能照映出事物的某些面相。其他面相,依然暗昧不明。若欲接近“主伴交辉,理事齐现”(法藏:《华严金师子章·勒十玄第七》)之境,惟有对同一事物,多构造几种理想范型,从不同方面反复切入,交互映射。内山先生的宋代诗人范型,已然发挥了它的解释力。另辟角度,建立新范型,则是后来者的任务。
末了,有两个小问题。本书第六篇(初发表于2015年)纵论唐人别集,以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为据(130页)。此书早出,著录唐集一百零八种;其后赵荣蔚先生又有《唐五代别集叙录》(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之作,著录唐五代集二百五十七种,去除少许五代别集,唐集仍多出一倍有余。倘据赵《录》立说,论点或能更趋精细。第八篇(初发表于2016年)称宋代别集在作者生前梓行,当推元丰二年(1079)前后问世的苏轼《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为首例(180页)。内山先生早持此说(《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试论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的关系》,收入《传媒与真相》,281页),可是他本人后续研究,已加修正。第六篇所举庆历六年(1046)刻印的李觏《退居外集》(146页),即远在苏《集》之前,而此篇犹袭旧说。殆因本书由论文编成,各篇观点偶未统一。附笔及之,谨供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