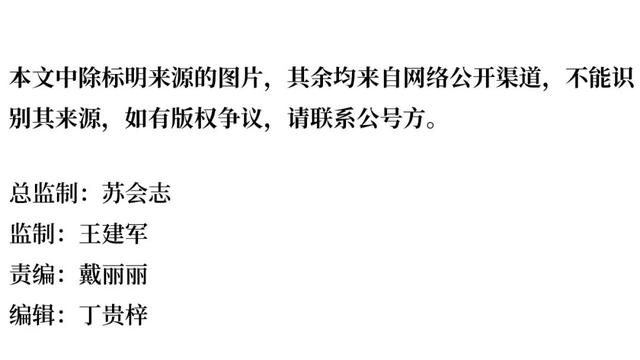何高勤这名字对命运如何的简单介绍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汶川,一场里氏8.0级特大地震猝然袭来,许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一些人永远留在了那一天,也有人幸运地拼出了一条生路,走到了今天。
13年,弹指一挥间。今天,库叔分享一篇北川一中幸存者张凤的回忆录,见证她一路走来的不易。
在那场地震中,她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失去了双腿,从绝望地认为自己无法再站起来,到可以自由在大学校园中行走,再到摇摇晃晃地去北京深造,在无数人的帮助下,她涅槃重生。她的背后,是无数有着相同经历的汶川人。
谨以此文,悼念逝去的同胞,也鼓舞幸存下来,仍旧努力生活的同胞。每一个春天都会来临,在你还觉得寒冷的时刻。
文 | 张凤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汶川十年》,华景时代2018年5月出版,原标题为《少有人走的路》,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废墟下的24小时
那是个晴朗的下午,有没有太阳我不记得,但一定没有下雨。我穿着前一天新买的浅蓝色针织两件套上衣和天蓝色的帆布鞋,在上课铃响前踏着轻快的步伐进了教室,在临窗倒数第二排坐下,从抽屉里摸出化学课本和文具盒。
我的同桌是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戴金属方框眼镜的幽默男生。我的前排是两个女生,一个内向安静,一个活泼开朗,前者叫张菊,后者叫张翠。我正好可以望见教学楼拐角突出的那一部分,还有操场上的国旗。
化学老师魏老师穿着黑底白花的孕妇装,她的肚子圆滚滚的,很可爱。她是一位耐心、温和的老师,对像我这样的差生亦是充满耐心,所以我最喜欢她。
老师在讲台上认真地讲着,我边听讲边写笔记。突然,一阵剧烈摇晃,玻璃窗“哗哗”地响。大家都停了下来望着窗户,有同学用开玩笑的语气高声说:“地震了。”大家一阵哄笑。老师看了看窗外便继续上课。可是不到30秒,整个楼突然又剧烈摇晃起来,而且没有停下来,我看见拐角处墙体一块一块往下掉,惊呆了……耳边传来桌椅挪动碰撞声、惊慌失措的尖叫声、脚步声……我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我看见天花板从中间呈放射状向四周裂开,掉了下来……教室中间凹下去一个大洞,我感觉身子一沉,掉了下去,我闭上了眼睛,担心着从四楼掉下去会摔死……

2008年5月14日,解放军战士在四川北川县中学的废墟里寻找并呼唤幸存的师生。图源:李晓果|新华社
就那么一瞬间,我着了地。剧烈的痛从我的脚下传来,似被人拿刀砍一般……空气中充斥着浓浓的混凝土味儿,睁开眼,四周一片漆黑,唯有右上方一个小孔透进来一点儿微光。我侧着身斜靠在椅子上,左手被压在右边的预制板下。背下软软的,我知道是我同桌,他一点儿生机都没有,我知道他走了……周围一片哭喊声,有男声,有女声……余震频频,我很害怕,但我并不想哭,我觉得我一定能活着出去,我一定要活着出去。在一片混乱声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叫着:“魏老师!魏老师!”可是并没有任何回应……旁边传来另一个啜泣的声音:“魏老师在讲台后,讲台倒了……”我又听见一个声音说地震什么什么的,我才知道原来是地震了,刚刚那一刻,我还以为只是教学楼塌了……
我听见有同学和张光辉对话。原来他因为离教室后门最近,所以当时立即跑到了过道上,而教学楼是向右下方坍塌的,所以他没有被掩埋。他告诉大家说:“擂鼓镇有吊车,等吊车来了就可以救大家出去了。”没过几分钟,又有同学问道:“吊车来了没啊?”他说:“快了。”不断有同学追问吊车何时能到,我也忍受不了腿疼,便问他:“吊车还有多久到啊?“快了,就快来了,高三的学生都没受伤,他们已经开始救人了。”听了这话,心中略微踏实些,我想我哥会来救我的。
不断有同学追问他,他一直答“快了”。后又说路断了,等路通了就来。我渐渐对这辆吊车失去希望,后来再也没人追问吊车的事了。
感觉不到一小时,哭喊声少了许多。我听见旁边有同学说:“别挤我,我好难受,我感觉自己透不过气来了!”“别挤啊!”一个男生哭着喊道:“爸,妈,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一个女生哭着对另一个女生说:“你出去以后,帮我告诉爸妈,我爱他们!”那女生哭着回答道:“要说等你出去自己说,我才不替你说。”
我感觉脚下又一阵剧烈疼痛,有一个人在我脚上,她一动我就剧疼,我知道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唐安阳。我说:“安阳,你别动,你一动我脚就好痛!”她并未搭话。我却因为这样一句话自责懊悔了许多年,我觉得自己真的好自私,在她人生的最后,不是关心她怎么样了,而是让她不要动,她一定特别难受才会动。我就让她一个人在孤独和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还自诩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我竟然这样对待我的朋友。我花了许多年才从心底真正原谅自己。

2008年5月13日,救灾官兵在北川县冒着遭遇塌方和余震的风险,克服重重困难抢救受伤百姓。图源:杨磊|新华社
我听见她像是在呕血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她喊了一声“妈妈我爱你”,然后再也没了动静,不知又过了多久,我用手去摸她,她已经凉了……那一刻,我只觉心头一凉,我最好的朋友,生命中第一个朋友,她死了……但悲伤的时间并不长,我便将她抛在脑后,心里只想着怎么才能出去,何时才能出去。
左边似乎是赵宗阳在呻吟,我问他:“赵宗阳,你怎么样了?”他说:“我头被压住了。”我流着泪大喊:“赵宗阳,你要坚持住,我们一起活着出去,一定要坚持住!”但他再也没有任何声音……
又不知过了多久,附近的家长来找他们的孩子。家长们边喊着孩子乳名或学名的声音边在废墟上移动。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叫“赵阳娃”,我知道是在叫赵宗阳,我犹豫着要不要搭话,若告诉他们赵宗阳在这里并且已经走了,他们能承受这个噩耗吗?不告诉他们,他们又会四处找。最终我还是没有喊住他们,怀着希望多找找,总比这么早知道噩耗强些。
我听见附近有一个叔叔在说话,我大声喊:“叔叔,你可以救我出去吗?”叔叔用双手扒开那个小孔旁的碎石,亮光透了进来。叔叔看着我说:“孩子,你埋得太深了,叔叔没法救你出来,但是叔叔可以把这个洞刨大些,这样你就不会被闷着了。”叔叔又用手刨了很久,那个只有拳头大的小孔被扒开脸盆那么大,然后叔叔就去找他的孩子了。
我可以清楚看见里面,从左前方到左后方,全是横七竖八杂乱堆积起来的预制板和碎了的混凝土块儿,后面是被压变形的桌椅混杂着碎石挤压在一起,足有一层楼那么高,电线露了出来,一块平整的预制板盖住了我的脚但并未压在腿上,预制板下面还有一些东西支撑着,刚好压在我脚踝的位置。
而这时我的腿已经完全不痛了……我的课桌在右上方,书本还整齐叠放在抽屉里,我用右手将它们扒拉出来,找到了我的日记本,我想要带着它离开这里。我看不见唐安阳,也看不见赵宗阳,更看不见我的同桌……

2008年5月16日,救援官兵在北川中学抢险救援。图源:杨世尧|新华社
我隐约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高声喊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的同学也帮忙喊道:“张凤在这儿!”可是没有任何回应。不知过了多久,天渐渐暗了下来,我的左手压在右边致使身体呈侧扭着的姿势,很不舒服,我用力拔出左手,手背一片血肉模糊,肿得如原来两个手掌叠加那样高,却一点儿也不疼。我感觉周围越来越安静了……
白天快要谢幕时,部队终于来了。两个军人来到洞口向里面问:“有人吗?”我满心欢喜答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出去了,却只见一个军人边用手指着预制板边对另一个说:“如果搬这边,全是桌子椅子,万一塌了很危险,那一边全是预制板,太大了,我们没有吊车,人力根本抬不动。”另一个人点头。
不断有人喊:“叔叔,救我!”“同学,我们要先救上面的同学,然后再救埋得深的同学!”我抬头望了望,我埋得真够深的!
天黑了,废墟上亮了一盏很大很大的灯,灯光从洞口射了进来,我偶尔可以望见外面移动的人头。可是我累极了,便昏昏沉沉睡去了。半夜,我被外面的号令声和余震惊醒。借助洞口透过来的光,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晚上十二点了。透过洞口,我看见雨密密地落了下来,像一根根细细的绣花针刺破斜斜的灯光,落了下去……再也没听见呼喊声和呼救声,我不知不觉又睡过去了……
后来被一阵熟悉的声音惊醒:“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坚持住,我们很快就救你们出来!”这个声音回荡在废墟上空,由远及近,我听出来是我们年级的历史老师廖光明。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大声呼喊:“廖老师,廖老师!”
“你是哪个班的?”
“我是高一(5)班的张凤!”
“张凤,你一定要坚持,现在吊车和氧焊切割机都来了,很快就救你出来!千万不要放弃!”
“好,我一定坚持住!”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心中一下子充满了信心、希望与力量。
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依然下着雨,我看手表,已经早上7点了。除了救援人员的声音和机器声,废墟安静极了。
我忘了又如何熬过两个小时,他们开始救张菊和张翠。他们用了两小时把预制板切开,再一块块搬开,直到周围成为一个巨大的坑,才将她俩小心翼翼取了出来。

2008年5月15日,消防战士在四川省什邡市蓥华镇云峰化工厂倒塌的宿舍楼废墟中营救出一名生还者。图源:姜帆|新华社
终于轮到我了。我看时间,已经中午12点了。可是我感觉自己已经很困了。叔叔先将浸湿的棉衣盖在我身上,以免氧焊切割机喷出的火花烫到我,然后开始一块一块切割预制板,又一块一块搬走。搬预制板时掉落的沙石“哗哗”往左耳朵里灌,我赶紧拿手掏耳朵,刚掏完沙石又灌了进去,我只好捂住耳朵。火星溅到了我身上,雨也开始落在我身上,又冷又痛,一阵强烈的困意袭来,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让眼睛睁着。我问:“叔叔,还有多久,我好困,好想睡觉!”
“孩子,千万别睡,很快你就可以出来了!”
我努力撑着眼皮,不让它们闭上。可是感觉自己越来越困:“叔叔,我真的好困!我想睡觉!”“姑娘,千万不要睡觉,你一定要坚持住!”
就这样在和叔叔的对话间,他们已经把我周围搬空了,像是被炸弹炸出一个巨大的坑。我看见一个已经离开的同班同学……我有些害怕。叔叔说:“闭上眼睛,别看!”他们拿来了担架,把我放了上去。我说:“叔叔,我的书你帮我拿着,我还要。”我看见他抱起一摞书,我便被四个兵哥哥用担架抬了出去,走到坑边,我看见往日的教学楼变成一堆碎石,上面散落着书包、衣服,还有淋湿的课本……
他们先将我抬到操场边的临时医疗站简单处理了一下,又把我抬到校门口,只用一床棉絮半铺半盖。我的右半边身体露在外面,雨落在身上,觉得好冷。我往左边蜷缩,想躲进棉絮里,一个叔叔看见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答:“我冷。”他便拿一条薄的棉絮给我盖上,又拿了块塑料布盖在最外面,我感觉暖和多了!
我看见周围地上密密麻麻坐了好多人,有的缠着绷带,有的并未受伤,但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悲伤与低落,没有人讲话。我听见雨拍打着塑料布,一阵又急又密的嗒嗒声,雨下大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叔叔说:“这个小姑娘先走,她伤得很重!”我心想:我伤得也不重啊!都没有流血,只是腿有点儿隐隐的痛。但是能尽早离开这里也好。救护车开了好久还没停下来。我问司机叔叔:“叔叔,我们要去哪儿啊?”“去绵阳。”“为什么不去县医院?”“县医院塌了,全被埋了!”叔叔平静地说。
原来地震这么严重!
2
九死一生
我被送到绵阳市人民医院后被安置在医院广场,一块用雨布搭成的临时病房里,护士拿来一瓶生理盐水给我挂上,又拿了两瓶矿泉水放在床头,叮嘱我少喝点儿水后便离开了。我右边是曲山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小姑娘,她津津有味地吃着八宝粥,尽管一天一夜粒米未进,我却一点儿食欲都没有。
我在那儿躺着,双腿隐隐地痛着,渴了便让旁边的人给我拧开矿泉水瓶盖,侧着头喝几口。躺了两小时左右实在难受,想要坐起来,挣扎了半天也坐不起来,只好让旁边照顾家人的阿姨扶我起来,可是扶起来以后我根本坐不稳,只好让阿姨背靠着我让我坐起来,坐起来后感觉舒服多了。我看见我的裤腿被挽到膝盖的位置,左腿的皮肤呈黑紫色,右腿颜色深紫,但是并没有流血或者破皮。我靠坐一会儿后又躺下了,不知不觉迷迷糊糊睡着了。

2008年5月13日,救援官兵抬着一位幸存的小姑娘爬上斜坡。图源:江毅|新华社
等我醒过来时,天都已经暗了下来,左边的男生和右边的小姑娘都不知去向,我的床头旁边坐着一个叔叔,我问叔叔是哪儿的人,他说北川县城。
“叔叔,你怎么不躺一会儿?”
“我腰受伤了,只能坐着。”
“叔叔,你有电话吗?”
“有。”
“可以帮我打一个电话吗?”
我从裤兜里掏出电话本递给叔叔。电话接通后,我妈说他们和村上其他人正在联系大巴车准备往学校赶。我说我现在在绵阳医院,我伤得不重,你们不用来了,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妈听见我的声音后显得激动还是担忧,或者都有,我也未曾注意,而那时我满心欢喜,觉得自己的伤不会有什么大事,根本不明白有一种东西叫“挤压综合征”。
【注:“挤压综合征”是指人体四肢或躯干等肌肉丰富的部位遭受重物(如,石块、土方等)长时间的挤压,在挤压解除后出现身体一系列的病理生理改变。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以肢体肿胀、肌红蛋白尿、高血钾为特点的急性肾功能衰竭。如不及时处理,后果常较为严重,甚至导致患者死亡。】
后来我又给好朋友红梅打电话,告诉她我在人民医院,让她过来陪我。她听见我的声音既欢喜又激动,她说第二天天一亮就过来陪我。通完电话后我怎么都睡不着,两腿隐隐的痛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就躺在那儿,听雨拍打着雨棚,嗒嗒嗒,嗒嗒嗒……天一直不亮,时间变得漫长。躺着实在难受,我又请负责管理雨棚的叔叔扶我起来背靠背坐了一会儿。5点时我又给红梅打了个电话,问她什么时候过来,她说天一亮就来。6点多她就匆匆赶了过来。她来了之后,先是和一些志愿者把我送到检查室拍了X光片,看手脚是否骨折,然后又把我推进大厅里,医生简单消毒后直接拿手术刀划开我的小腿,我却一点儿都感觉不到疼痛。
而此时,时间已经到了5月14日的中午,我仍然一点儿胃口都没有,我的床头已经堆了一大堆医院发的速食食品。红梅劝我吃些东西,可是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想吃,她问我想吃什么,我突然想到酸酸甜甜的葡萄,便说要吃葡萄,她就去买了。感觉她走了好久才回来,回来时拎了一串提子,我吃了一颗,觉得硬硬的,不酸也不甜,便不想吃了。后来医院又给伤员发了香蕉,她剥一根香蕉给我,我咬了一口,觉得又生又硬,便吐了出来。
红梅一直劝我多少吃点儿,说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一个路过的老奶奶看见便问我要不要吃菜叶稀饭,她回家给我做,我想到以前家里的稀饭瞬间很想吃。可是等了好久好久,奶奶才端了一碗稀饭过来,我吃了一口,完全不是想象中和记忆中的味道,所以也不想吃了。红梅万分着急,而我是真的一口也吃不下。
到了晚上,我极其困倦,医生却叮嘱他们千万不能让我睡着,不然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所以红梅一直不眨眼地盯着我,我一闭眼她就拿手轻轻拍我的脸,把我拍醒。到后来,聊天已无法使我清醒,我便在那个广场上唱起了我们羌族的祝酒歌,那是我长这么大,唯一一次在众人面前放开了嗓子唱歌,没有一丝害羞与顾虑。

2008年5月14日,解放军某部医护人员在北川地震灾区救助受伤群众。图源:赵颖全|新华社
再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快到中午的时候爸妈打电话说他们到了,立刻去找了医生,医生说我腿压的时间太长了,必须做左小腿截肢手术,爸爸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哭了,我只听见妈妈略带训斥的声音:“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我以前没有看见爸爸哭过,这是我长这么大唯一一次知道爸爸还会哭。而我知道截肢就是要把我的腿锯掉一截,但那时我还不明白截肢意味着什么,所以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事。
什么时间、在哪儿做的手术,我完全不知道,等我清醒过来,我已经在医院楼道里的病床上了。几个远房亲戚过来看我,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草莓。刚好医生从旁边经过,对我爸妈说:“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儿,再买件新衣服,万一不行了,不能光着身子走啊!”又对身边的护士说:“你去给小姑娘买点儿草莓。”
所以后来我就有了两筐草莓。
挨着我病床的一位老爷爷被推走了好久都没有回来,爸爸找了护士把我放到了那张病床上,我才算是住进了病房。到傍晚时在哈尔滨上大学的海哥坐飞机回来看我,他们都坐在病房门口,一言不发,也不吃饭。我虽然没有胃口,倒是很喜欢草莓,一会儿要直接吃,一会儿又让我妈帮我拿白糖拌着吃。
虽然才5月中旬,病房里却异常闷热,需要人一直不停为我扇扇子,我才感觉到些许舒服。我感觉到伤口分泌的液体已经打湿了床单,还散发出阵阵腐肉的气味,好像自己已经开始腐烂了一样,也许人死后被埋在地下腐烂时就是这样的味道。
第二天,也就是16号,红梅和海哥去城里给我买衣服,花了一上午,跑了大半个城市,给我买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穿着裙子离开是我那时的心愿。那天下午我突然想起安阳的妈妈可能正在四处找她,就让爸爸给阿姨打了电话,我告诉阿姨:唐安阳不在了。阿姨发疯似的冲进我的病房,扑向我的床,边哭边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爸爸妈妈把她拉了出去。我虚弱得说不出话来,但是看见阿姨那个样子心里难过极了。这些年,我一直想着去看看阿姨,告诉她安阳临终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妈妈我爱你!”可是我一直不敢面对她,也害怕她看见我伤心难过。
也是在这一天,由于双腿受挤压严重引起了急性肾衰,医生开始给我做血液透析。做血透的过程中,我感觉脖子插管子的地方特别疼,后来我就睡着了。等醒过来后,我看见爸妈紧张地望着我,我说:“发生什么事了?”爸爸说:“女儿,你吓死我了,你刚刚昏迷了。”“啊,我只是睡着了啊。”一整天医生忙得脚不沾地,换药还得自己去找医生,不然医生根本记不得或者腾不开时间。
17号早晨,医生在病房对我爸妈说:“孩子的情况很危险,留在这里估计不行,如果能转院的话倒是还有希望!”爸妈说:“要转院,我们要转院。”
“今天就有一批救护车来,接一批伤员到重庆去。”我想到要去重庆,心里都乐开了花,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远门。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再从中午等到下午,救护车一直没到,临近晚上才到。

2008年5月13日凌晨,救护车辆在都江堰市运送伤者。图源:杨磊|新华社
一路上,十多辆救护车的鸣笛声此起彼伏,到了医院已经是半夜了,许多医生护士等在门口,我被抬上一张移动病床,在黑夜中,我感觉自己先是上了一段很长的斜坡,接着就是一段短而较陡的斜坡,然后进了住院部大楼,进了电梯,到了骨科病房。三张病床整齐地排列着,每一张病床旁边都放着一个立柜,立柜上摆了花瓶,每个花瓶插了一枝康乃馨。我被安排在中间的病床上,而我旁边的那枝康乃馨却已经接近枯萎。
我妈当时心里就觉得那是个不祥的征兆,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我在5月17日深夜转入重庆三二四医院,住进住院部三楼的骨科病房,又过了几天因为经常需要透析,又转到泌尿科。泌尿科是一幢独立的两层楼房,在这里我认识了众多关爱我的医生、护士,有泌尿科主任孙叔叔、主治医生舒勇哥哥、护士长高勤姐姐、护士李俭(俭妈)……第一次见孙叔叔,他问我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我说我想喝可乐,冰冻的那种。他就让护士给我买了两瓶冰冻可乐,并且吩咐一瓶拿给我,另一瓶先放入冰箱冻起来。从此以后,孙叔叔对我特别好。有一次晚上8点多他才从手术室忙完出来,就来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凉拌黄瓜!”他就开车回家拌了黄瓜又开车给我送过来。
后来我又转回骨科病房。一个下着滂沱大雨的夜里,我突然呼吸急促,他们给我盖棉被,把我推去泌尿科做透析。后来我的饮水量被控制得更加严格,计算每种饭食的含水量,我每天摄入的总的水量不能超过100mL。我渴了就拿棉签蘸水涂涂嘴唇。所以我总是想尽办法获取水分,那段时间我超级爱吃稀饭和西瓜,伤口愈合之后就再也不想吃稀饭了。当然我还干过很多他们不知道也不允许的事来获取水分。
一次,我趁着我妈不注意,一把抓过柜子上的优酸乳猛吸,等我妈反应过来夺走时,我已经喝了半盒。
因为我经常发烧,所以他们会给我一个医用冰袋拿在手里,有时是塑料袋装的,有时是塑料瓶子装的。要是塑料袋我就咬破一个小洞,然后吸化了的水,有时运气不好,用生理盐水冻的冰就特别咸。要是塑料盒子装的就只能舔舔外面,要是被发现我就说是在给脸降温。
病情一严重我就吵着要冰棍,我甚至还在深夜大家都睡着后偷吃过果冻。
没多久我就接受了第二次左腿截肢手术,这一次由于感染严重,截到大腿的位置。然后采用一种进口材料覆盖我的右腿,将分泌物和瘀血引流出来。大约一周以后,右腿颜色渐渐转为正常。大家都很欢喜,但是当张叔叔让我动一动右脚的脚趾头时,我只能动整个脚掌,却动不了脚趾头。
于是张叔叔拿手术刀把我的右小腿后侧划开,并且让我爸看:“肌肉全部坏死了,像煮熟了一样。”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当时并不担心。第二天下午我一个人在血透室,张叔叔过来和我说要把右腿也截掉,不然我会有生命危险。我“哇”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那样我就一条腿都没有了!”张叔叔说:“昨天我也让你爸爸看了,里面的肌肉都坏死了,如果不截,你真的会很危险。”我觉得张叔叔说的很有道理,哭了几声也就不哭了,到那时,我依然不知道截肢真正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双腿高位截肢。那时所有人都围着我转,很多人来看望我、关心我、爱护我、表扬我,给我买玩具、好吃的,长那么大,我从未那样快乐过。所以除了伤口疼痛和不能随意喝水外,我都是开心的。
第三次截肢手术后,我又被转回骨科。
一个下午,我突然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心率接近130bmp,我感觉己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可能马上就会死掉。
【注:心率正常值为60-100bmp。】
那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医生给我打了麻药,用一根扁平细长的针从肋骨间插了进去,抽出一大管淡黄色的液体,他们说那叫胸腔积液。后来他们又把我送去做核磁共振,在路上我说:“我想见我哥,我感觉自己要死了。”廖老师安慰我说:“等伤好了就可以见哥哥了。”可是我感觉自己好像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病情并没有好转,因为伤口感染病情加重,心肺功能也开始衰竭,我变得特别虚弱,于是医院给我增派特护三班倒专门照顾我,每天都用紫外线给房间消毒,外人不得探视。没多久我就转入呼吸科,依然一个人住一间病房,外人不得探视,我爸妈也不能在病房久留。
要是护士不在,我就躺在病床上,来看望我的人只能透过门外窗户边望一望便离开了。
我十分渴望有人能进来陪我聊聊天。
一次一个老奶奶看见没人便推门进来问我想不想吃茶叶蛋,其实我不想吃,但觉得能有人说说话很好,就说想吃。老奶奶拿来茶叶蛋,边剥边和我聊天。不一会儿护士回来狠狠批评了老奶奶一顿,让她离开了。
长期待在病房里,感觉自己像被困在笼子里的小鸟,特别渴望能到外面去吹吹风、淋淋雨,所以每一次去泌尿科做血透时,我都央求他们让我在门口那棵树下停留一会儿,可是他们往往都只停留一下就急急把我推回病房了。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窗外响起了国歌,那是旁边的十八中学在举行升旗仪式,我突然感到心里阵阵发热,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伴随着一种莫名的感动从心底升起,从小学一年级起,参加过无数次升旗仪式,我从未有过那样庄严而神圣的感觉。我突然间特别想念老师和同学,想马上回到学校,回到他们身边去。

2008年5月24日,解放军战士和四川青川县“猛虎”爱心帐篷小学的师生们一起参加升国旗仪式。图源:刘海峰|新华社
某一天傍晚,在护士长高姐姐给我洗完头后,我突然高烧不退,继而眼睛也看不见了,恍惚中只看见一颗正五边形彩色星星就在我眼前转。我听见他们去请了五官科医生来检查,让爸爸过去签病危通知书。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和外部损伤,突然我感觉黑暗中一只大手向我伸来,我努力想要躲开……后来我妈说我那时癫痫发作,拼命挣扎,把伤口都挣开了,流了好多血,他们几个人都按不住我。后来他们把我转进了重症监护室,护士一直不停地给我擦酒精来退烧。到后半夜醒来,我的眼睛才又看见东西了。
第二天,我又被转回泌尿科。泌尿科从日本进口了一台新的血透机,还请了两位技术人员来指导使用,新的血透机的透析速度特别慢,以前血透只需要两小时,现在需要大半天,而且一旦病人情绪激动,机器就会报警。
下午,西南医院一位资深老专家过来,一大群人围在我的病床前讨论着,然后他们把我的绷带拆开了,那感觉就像是有人拿刀在割我腿上的肉,我边喊痛边挣扎,机器就不停地报警,小姐姐一直安抚我,让我别激动,可是真疼!他们看不下去就给我打了麻药,疼痛的感觉才有所缓解。后来很多次换药都必须打麻药。
后来孙叔叔告诉我:“那个老专家说要是你们三二四医院能把这个小姑娘救活,你们就算是发射了一枚火箭!”那意思大概是他们想救活我比发射一枚火箭还难。但孙叔叔说他坚信一定能救活我!
熬过了那几天我就渐渐好转了,终于可以排尿了,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激动极了,护士长姐姐后来告诉我:“那时再也不觉得尿是脏的,觉得它是那么宝贵。”因为能排出尿,表示我的肾功能恢复了。我的伤口也渐渐愈合,那时是6月中旬。6月下旬,我左腿又做了一次修复手术,7月初我几乎痊愈了。
7月上旬我离开三二四医院,走之前和大家一一合影。离开时,心中恋恋不舍,到今日已经10年了,我们依然联系紧密,我会一辈子记得和他们在一起的温暖时光,而重庆也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重生,我的身体里流着一半重庆人的血。
3
漫漫复健路
在废墟下我只想活着出来并且坚信自己能活着出来。等到了医院依然只想着活下来,即使两条腿都高位截肢,即使每天换药都钻心地疼。但是到了四川假肢厂一切都变了,每个康复医生要管好几个病人,我时常无人管理。
每天反复做着同样的训练,仰卧起坐、燕子飞就练了一个月,戴上假肢后光是站立就练习了两周,枯燥而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每天到点就去训练室,经常坐在那里出神,甚至直接睡觉。到后来能出去走了之后,积极训练了几天,走几步就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两个月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所以也没了积极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推着轮椅出门,一路上不断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有的人甚至停下来久久打量着我,就像打量一个怪物……他们的目光灼伤了我脆弱敏感的心,我每次都还以恶狠狠的目光。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双腿截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奔跑,甚至连一般的走路都做不到,如果戴上假肢训练得好基本能行走,许多事从此便与我绝缘,漂亮的短裙、高跟鞋……我变成了一个敏感的小怪物,训练时偷懒,对父母发脾气,和医生顶嘴……偶尔心情好努力训练,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呆,有时还会生气将假肢丢开……半夜睡不着时,我总会想起安阳和宗阳。
有天晚上我梦见安阳回来了,我特别高兴,跑过去和她说话,可是她并不理我,还在为我的自私生气,我又惭愧又伤心,只好在一旁默默流泪,哭着哭着就醒了……我想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了。
但是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个传奇女人——王志航,她成了那段痛苦康复路上唯一的美好,后来成了我的干妈。十年之间,她的坚强勇敢,她的热情,她的真诚,她行走于世间的侠气,她考虑事情的细致周到,她待人的宽容大度,她指点江山的气魄……一一感染着小怪兽。小怪兽渐渐长大了,学会了真正的感恩,学会了付出,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温柔,也学会了为别人考虑。
【注:王志航是一位来自成都的志愿者,在汶川地震后成为200多个伤残孩子的干妈,2017年,她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

为了能让孩子们从心理上站起来,地震过后,王志航(中)经常带领张凤(右)等在康复中心治疗的孩子们去练习游泳。图源:余坪|《汶川十年》
训练到2009年1月份,我终于又回到北川中学在长虹培训中心的板房学校。拄着双拐勉强能走平地,大部分时间还用轮椅。
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处处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吃饭需要人打回来,衣服需要人洗,连上厕所都需要人陪……我渴望自由,身心的独立自由,我希望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自己就经常练习走路,到了高三回到新学校就基本不用轮椅了,到了大学就完全不用轮椅了,虽然走路摇摇晃晃的,但基本可以独立生活了。现在,我可以拖着行李箱一个人摇摇晃晃地闯荡江湖了。
回到北川中学,班主任罗老师对我特别细致体贴,由于我总是情绪有波动,罗老师带着我去了“安心屋”,我认识了张阿姨。我们第一次谈话,我就告诉张阿姨我和安阳的故事,而且地震后我再也想不起她的样子。张阿姨让我抱着一个海豚公仔,闭着眼睛去想象她的样子。
我闭上眼,仿佛看见我们两个走在两栋学生公寓之间,她扎着马尾在前面一蹦一跳地走着,怎么叫她她也不回头。我大声哭着告诉张阿姨:“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见她的背影。”“把你想说的话告诉她。”我拼命对她说:“对不起!”但她依然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想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之后,张阿姨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这么多年来,每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我总会联系张阿姨,而她总能给我力量与温暖。我从高中起就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像她一样的人,能带给别人许多温暖和力量。
4
守望与成长
地震后第一个清明节,张阿姨带我回了北川中学,在那个新修却还没有完工的运动场上,在雨中,我坐在轮椅上俯瞰整座废墟,书本、衣服、书包散落在各处,那些同学就长眠在这里了,他们永远16岁,而我还会一点点长大……浓浓的悲凉萦绕心头,那么多同学都死了,我为什么还活着?
连续几年清明节我都会回到那里。第二次回到那里,一条醒目的横幅如同一根刺扎进我的心,上面写着“沉痛悼念爱女——母灵芝”,那也是我同班的一个坐在我附近的女孩子。再次回去,原来的废墟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大土堆,看不见一丝曾经的痕迹,就如同我的过去被别人埋起来了。

2014年5月11日,一名小朋友在北川老县城祭奠。当日,陆续有北川群众和从各地赶来的人们在北川老县城悼念在汶川地震中遇难的亲友,寄托哀思。 图源:薛玉斌|新华社
从高一开始我就立志要读心理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复读一年后,我考上了成都师范学院。
去成都师范学院,离开那群共同经历生死的同学,我时常独自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怀念高中时光,怀念那些我可以在他们面前哭在他们面前笑的高中同学。
大一下学期,我读了《挪威的森林》,书中主人公先后失去挚友、至爱,他在经历一段低迷和痛苦之后重新活了过来。然而,我却彻底陷入痛苦之中,不断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总有一天要死的,既然都要死,早晚不都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我甚至觉得我如果得不到一个答案,我就没法接着活下去。我就想啊想,想着假如自己死了,我的朋友得多难过,我的父母、我的干妈得多伤心,他们为我担忧了太多,我不忍使他们再因我而伤心,所以我不再去想死的事。
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为了更好地死去,所以要好好活!虽然人都有一死,却是不同的死,有圆满的死、凄惨的死、迷茫的死、孤独的死,而我希望我死时,不会带着遗憾和痛苦离开。想到这儿,便豁然开朗。
2016年,我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生,在北林学习的一年,内心又经历一次震动。因为奶奶病危,我之前没有处理好的分离场景统统涌现出来,我一想到奶奶可能会离开,就止不住地流泪。我想到安阳,想到挺过地震却因突发心脏病而离开的王飞,想到地震后不久病逝的爷爷……他们都是突然离开,都没来得及告别,那些悲伤都一直堆积在我内心的角落,现在的分离危机将往事统统带了回来。我感觉自己如同那光秃秃的柳枝,像枯死了一样,我对干枯的丁香丛说:“你们死了,我的一半也就死了……”

2016年6月19日,张凤收到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图源:《汶川十年》
我约见了咨询师,在他的帮助下,我“回到”2007年冬天的北川一中,进入校门,那两排树木依然整齐挺拔,一切像是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整个校园空荡荡的,但空气中却弥漫着动人心魄的紧张,四处散落着湿漉漉的黄叶,操场角落那株蜡梅散发出冷冽的清香,而教学楼花坛前那株蜡梅只剩下一丛树桩,我攥紧拳头,小心翼翼地走上四楼,来到教室,课桌依然整齐排列着,却没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我在门口向里望了望,并不敢进去,我无法忍受自己的紧张便快速跑下楼去,穿过操场跑向校门口……
第二次,我“回到”2007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我看见大家在雪地里欢呼奔跑,我捡起一个雪球砸向同学,然后快乐地跑回教室,我看见大家整齐地在教室认真学习,一下子热泪盈眶,他们都在,每一个都在,魏老师依然穿着那件黑底白花的孕妇装,安阳靠在课桌上傻傻地望着我笑,飞妈立在她身旁,宗阳就那样看着我,张翠还是那么傻乎乎的……
一时间大家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走进教室走上讲台,我对大家说:“好久不见,你们都好吗?”大家纷纷靠了过来把我围在中间,我一个一个对他们说着那些没有来得及说的话,那些遗憾,那些抱歉,那些愧疚,那些不舍……他们都温和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他们轻轻地摇头,让我不必难过和抱歉,他们过得很好,他们在一起很开心,他们会一直在天上看着我陪着我的……我说:“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们,你们永远活在我心里!”他们送我到校门口,我和他们一一拥抱再见,是那么不舍……
回到现实,我感觉心头的重担轻了至少一半,我终于和他们告别了。我可以轻松前行了,带着他们的祝福前行。我知道前方有许多荆棘,但是我并不害怕,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前行。

图为映秀的汶川大地震纪念馆。图源:翟子赫|新华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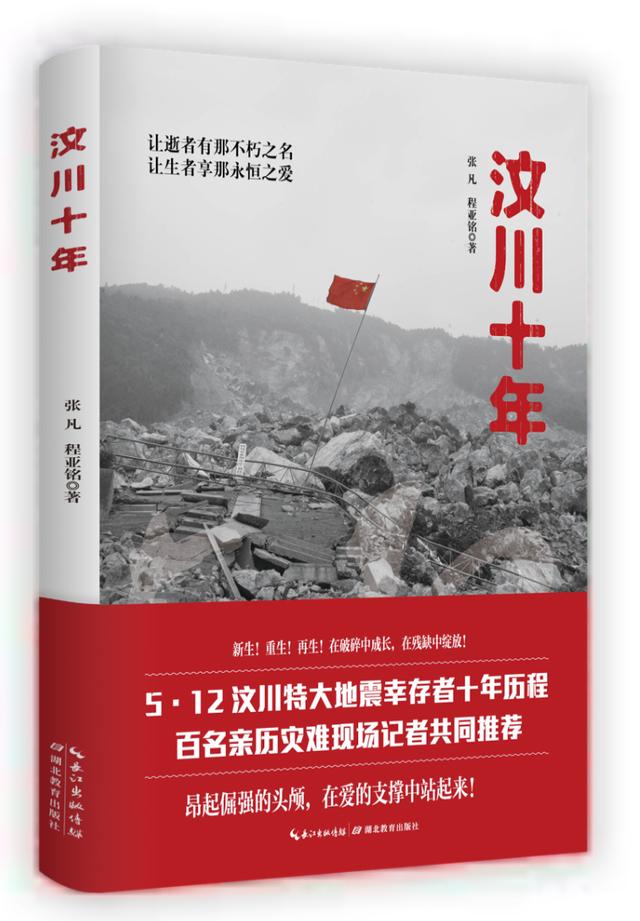
《汶川十年》
华景时代
汶川特大地震幸存者十年历程,
在破碎中成长,在残缺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