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2002年九月出生的马命运如何的词条
20年后的今天是“9·11”事件的20周年纪念。相较于以往,近期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重新掌权使得此次纪念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就在“9·11”袭击发生几个星期后,美国就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随后,则是伊拉克战争。从某种意义上,“9·11”事件深刻影响和重塑了国际政治的格局。不过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它首先也是一场人道主义的危机:众多的平凡人在这场飞来横祸中丧失性命,活下来的人,也大多难以摆脱灾难的阴影。他们的声音,不应该在每次灾难的纪念中被淹没。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一位喜剧演员曾评价:所有的笑声从此不合时宜。一位喜剧演员确实表示自己再也难以找到表演的冲动,一位当时在岗的少校再也难以摆脱保持警觉的状态,一名在事件中被重创的普通机场工作人员表示,过去的那个自己已经死在了2001年的9月11日。
米切尔·祖科夫事无巨细地帮众多的遇难者、遇难者家属、幸存者记录了“9·11”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并将其写在《坠落与重生》一书中。他是许多“9·11”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也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2001年他还在《波士顿环球报》担任记者,并于“9·11”事件当天报道了该事件并撰写了头条新闻。通过深入采访获得的大量细节,祖科夫让我们走进“9·11”事件阴影下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自2001年的那个清晨起所经历的那些坠落与重生。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坠落与重生》,有删节,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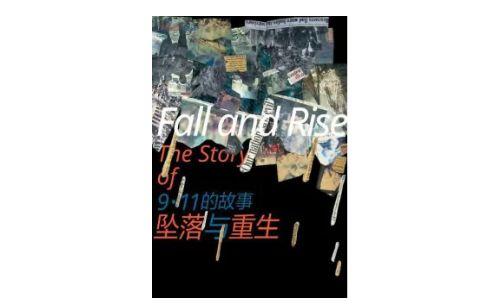
《坠落与重生:9·11的故事》,作者: [美]米切尔·祖科夫,版本: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2021年1月
受伤的美国东海岸,9月12日的早晨清澈温暖。袭击敲掉了美国金融中心的两颗门牙,损伤了美国的军事大脑,给它乡村的肉体留下了疤痕。“后9·11时代”的头几个小时,浓烟仍然在上升,泪水仍然在流淌,余震仍然在痛苦的中心不断回荡。它们震撼了股票市场、礼拜场所、学校和政府机关、机场和体育场、人心和灵魂。
袭击发生几个星期以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冲突仍在继续。随后是伊拉克战争,2003年开始,2011年正式结束。在决心发动这两场战争之前,布什总统发表了一则声明,事后,人们常常忽略这则声明:“美国的敌人不是我们众多的穆斯林朋友。美国的敌人不是我们众多的阿拉伯朋友。我们的敌人是激进的恐怖主义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它们的政府。”
追杀本·拉登用了整整十年,于2011年5月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达到高潮,本·拉登被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杀死。据称是9·11策划者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于2003年被擒,中央情报局对他严刑逼供。他和另外四个人被指控训练、资助和指挥那些劫机犯,在美国位于加勒比地区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关了十多年,受审日期还未确定。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国家需要统计死伤人数。起初,人们还充满希望,整个曼哈顿到处张贴着“寻人”启事。但很快,他们就明白,那些失踪人士永远消失了。死亡人数不像最初想象的那样高,但是,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在袭击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就说过:“最终,死亡人数肯定超过我们任何人能够忍受的程度。”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除了劫机分子,已知总共有两千九百七十七名男女老少在四架飞机、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遇难。遇难者中,有一千四百六十二人在北塔,六百三十人在南塔,四百二十一名纽约紧急反应人员,二百四十六名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还有五角大楼的一百二十五名男女。尚克斯维尔的地面没有人员伤亡。
大约六千多人身体受伤,其中有一些人永远不会康复。还有几千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紧急反应人员和调查人员,得了呼吸、心理和其他方面的疾病,这些疾病在后来才出现症状。9·11过去将近十七年后,联邦调查局宣布负责亚特兰大局的戴维·勒瓦利去世,他曾经花了几个星期调查这次袭击。“戴维是在工作岗位上牺牲的,”联邦调查局宣布,“这是他在世贸中心工作的直接结果。”几个星期以后,纽约消防局负责搜寻工作的局长死于可以追溯到世贸中心毒素的癌症。罗纳德·斯帕达福拉是纽约消防局第一百七十八位死于9·11相关疾病的消防队员。谁也不会以为他是最后一位。当局估计,到9·11二十周年时,死于与世贸中心爆炸有关疾病的人数将会超过死在攻击中的人数。
统计死伤人数后还需要通知亲属。妻子们失去丈夫,丈夫们失去妻子,父母失去孩子,兄弟姐妹失去兄弟姐妹,朋友们失去朋友。损失也殃及祖父祖母、教父教母、叔叔阿姨、表兄弟姐妹、同学、邻居和同事。每一次死亡都会剜开一道粗糙的伤口。受伤最深的是一些孩子,他们之前并不懂得生命损失是永久性的。9·11中,大约有三千名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失去父母一方,包括一百零八名在父亲去世以后才出生的婴儿。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某种解释。
1
“你妈妈现在在天上,她现在是天使了”
约翰·克里默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一家非传统高中教数学,他的学生都是以前退过学的,或者是未成年妈妈,或者是英语有问题的学生。9月11日早上,一名助教告诉约翰,一架飞机撞中了世贸中心的一座楼。新闻让他难受,但他没有担心。他知道妻子塔拉在一架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美航飞机上,不是飞到纽约。
几个小时以后,约翰在一个没课的时段里和一名管理员一起给学校办件小杂事。约翰没有手机,不过管理员带着一个呼机,如果有人找他们,上面会显示一个号码。突然,呼机上显示9-1-1,管理员担心,他没有告诉别人就私自离开学校,可能惹麻烦了。
“这里离我家不远,”约翰说,“我们去那儿打电话。”
约翰给学校秘书打了电话,向她保证,他们马上就会回来。但是,呼机上的消息和学校的规章制度无关。
“你在那儿等着,”秘书多里·勒梅告诉他,“你爸爸会过来。”
约翰的脑海中闪过他儿子科林和女儿诺拉,他们都在托儿所里。
“怎么啦?出事了?”
多里把电话交给约翰的爸爸格里,格里负责管理这所学校。他从塔拉的妹妹莫琳那里听说了美航11号的情况,莫琳是从另一个妹妹凯莉那里听来的,凯莉和塔拉一样,也在那家大零售商TJX公司工作。
“你在哪儿,约翰?”格里·克里默问。
“我在家。”
“在那儿等着。我过来。”
“为什么,爸爸?”
格里不愿意说。
约翰在车道上等来了他的父亲,身后是他和塔拉用爱填满的漂亮黄色科德角风格小房子。
“塔拉的航班撞上了世贸中心,”格里说,“塔拉就在那架飞机上。”约翰瘫倒在父亲的怀抱里。
第二天,9月12日,好像约翰认识的所有人,加上很多他不认识的人,都聚集在他们的房子里,在永远不再是一个家的房子里。家人,新老朋友,TJX和伍斯特各个学校的同事们,记者和摄影师,还有带着炖菜和慰问的邻居们。
所有人都在,除了塔拉。
约翰和格里开了一个小时车到波士顿,回答联邦调查局的问题,后者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尽管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主要嫌疑犯,调查人员还是不愿意忽略任何其他可能的动机。回家之前,约翰去找了一名儿童心理学家,寻求如何把消息告诉孩子们的建议。约翰和父亲到家时,看见自己的母亲朱莉抱着一岁的诺拉,诺拉对眼前的一切混乱毫不在意。四岁的科林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小男孩继承了妈妈开朗的笑容,但是现在笑容消失了。约翰把他带上楼。
父子俩躺在约翰和塔拉的特大号床上,身下是塔拉姨妈做的有互锁环图案的婚被。“我得跟你谈一谈。”约翰告诉科林。约翰打开一包彩色蜡笔,摊开两张纸,画了一个带着天使翅膀的棕色头发的女人。然后,他帮科林画了一幅“天使妈妈”的画。
“出了一件事故,”约翰说,一边忍住抽泣,“你妈咪现在在天堂,她不回来了。她就在天上,现在是天使了。”
几个星期以前,塔拉用类似的话帮助科林理解为什么他只有一个祖母。塔拉不知道她说清楚了没有。现在,约翰不说话了,科林开始抽泣。他终究还是懂了妈妈的话。
门的另一面,朱莉痛心地听着科林嚎哭了一个小时,约翰试着安慰他。科林后来睡着了,依偎着他的父亲,在他父母的婚被上。后来,约翰把塔拉的长毛绒睡袍放在诺拉的摇篮里,让她闻着母亲的气味睡觉。
几个月后,约翰·克里默收到了纽约医疗检测中心的电话。对遗骸的DNA测试,辨认出塔拉一只脚和一侧乳房的一部分。几个月后,约翰又收到了更多关于遗骸的电话。约翰把他们找到的塔拉遗骸埋葬在伍斯特圣约翰公墓,这样他和孩子们需要安慰的时候可以去那里吊唁。每年的母亲节,他们都带着鲜花前来。
很多年过去了,验尸官一次又一次地打来电话。约翰告诉他们,不管再找到什么,请把它和其他遗骸一起埋葬在曼哈顿下城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博物馆会在十周年时对公众开放。受害人的遗骸被保存在纪念馆深处一间僻静的贮藏室里,旁边是一间仅对9·11受害者家人开放的静思室。
附近,在地面之上,有两个巨大的纪念池,就占据着消失的双子塔的位置。所有9·11已知遇难者的姓名,加上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事件中六名死者的名字,都以铜字刻在池边的矮墙上。晚上,灯光在每个名字的字母间闪烁。
俯视着纪念馆的是一座叫世贸中心一号的大楼。这座大楼高一千七百七十六英尺,选定这个高度是因为它的历史意义*,2014年10月开放时,它是西半球最高、全世界第六高的摩天大厦。大楼的主人一边庆祝它在建筑上的辉煌,同时也承认导致这座建筑得以建成的可怕背景。他们的广告说大楼拥有“远远超过纽约市建筑规范的人身安全系统”。
约翰·克里默再婚了。他的妻子蒂娜第一个说,塔拉永远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科林长大成人了,他经常说,母亲是他在生活中追求成功的动力。诺拉不记得妈妈,但在长大的过程中,她一直沐浴在关于妈妈的故事的温暖中。等到结婚时,她准备戴上妈妈的婚戒。
约翰和家人买了一幢俯瞰一汪湖水的新房子。约翰把那座黄色的科德角风格房子卖掉了。新房主答应他们永远不会抹掉地下室墙上用白油漆写的大字:塔拉❤约翰。

《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作者: (美)劳伦斯·赖特,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5月
2
“我们正在制定的政策,
是不是在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加激进?”
9月11日,安德烈娅·勒布朗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拉伊市准备上班,一名木工朋友在外面干活,盖一个新阳台。木工从广播上听到一架飞机撞中北塔,于是他喊安德烈娅,并跑到屋里打开电视。他们看着第二架飞机撞中南塔。
“可别在那架飞机上,”安德烈娅祈求着,“别在那架飞机上。”
就在她面对着罗伯特的死亡时,她渐渐相信,罗伯特最不想要的就是有人因为他的缘故而受苦,无论是谁,无论在哪儿。她采取了一个连她都承认不受欢迎的立场:更糟糕的回应是更多的暴力,于是,她和一些受到9·11影响的同伴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9·11家庭祈愿和平未来”的反战组织。这个名字来自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一句名言:“战争是把坏凿子,无法雕刻出和平的未来。”
这个团体在描述其历史的网页中写着,团体成员相信“夺走他们亲人的暴力有可能会失去控制,恐惧有可能会被政治家和媒体操纵,用来为有可能加剧暴力、在未来一些年间削弱美国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外交和国内政策做辩护”。
就像安德烈娅所说:“显然,我们很快就会去轰炸阿富汗,我为那里的人感到难过。那里的年轻人究竟怎么了?是哪些可怕的事件把他们造就成愿意屠杀无辜平民的人?……肯定发生过特别可怕的事情,或许是环境,或许是基因,或许是社会,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应当担负一些责任。这是现在最吓人的一件事:我们正在制定的政策,是不是在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加激进?”
修补五角大楼损坏部分的项目飞速启动了,名为“凤凰项目”。三千名建筑工人为自己定了一年的完成时限,这个期限与七亿美元的合同无关。戴着安全帽加班加点的人中有一个叫迈克尔·弗洛科的钣金工人,他唯一的孩子—二十一岁的军士马修·弗洛科在五角大楼袭击中死亡。新建的四十万平方英尺的第一工作区有全新的安全性能,包括安装在墙上和门上的明亮的“出口”标识,离地面只有几英寸,这样在浓烟中爬行的人也能看见。
在2002年9月11日的建成仪式上,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宣布:“今天,我们在此纪念在这个地方去世的人,并将我们自己再次投入到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人类自由的事业——中去。”
演说后面,拉姆斯菲尔德说:“未来的路还很漫长。尽管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我们知道,在一种意义上,那些对我们发起进攻的恐怖分子已经失败了。我们在阿富汗打响第一枪之前,他们就被打败了。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达到目的。恐怖分子想把9月11日变成一个无辜群众死亡的日子。这一天没有变成无辜死亡的日子,而是成了英雄诞生的日子。”
3
“我是夜晚温柔闪烁的星星。
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
除了77号航班上的五十九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外,五角大楼袭击中的遇难者有一百二十五人。其中,七十名是文职人员。九十二名五角大楼受害者死在第一层,三十一人死在第二层,两名在第三层。死去的人中有卡伦·瓦格纳中校和一级准尉威廉·鲁思,他们显然死于吸入烟雾,两人和约翰·瑟曼少校一起躲在一间办公室—他们死于那里,但瑟曼少校幸存下来。
有五名五角大楼受害者的遗体一直没有找到,其中四名在大楼内部工作:退休的陆军上校罗纳德·戈林斯基,五角大楼的文职工作人员;海军一级军士罗纳德·赫南威,他身后留下三岁的儿子和一岁的女儿;詹姆斯·T.林奇,海军的文职工作人员,因为喜欢在五角大楼的过道里发放糖果而为人所知;还有朗达·拉斯穆森,陆军的文职工作人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第五个是77号航班上最小的乘客:三岁的达娜·法尔肯伯格,头发鬈曲,喜欢公主,和她的父母、姐姐死在前往澳大利亚的途中。
废墟中还发现了飞行员奇克·伯林盖姆随身带着的塑封祷告卡,它被火烧了,但卡上他母亲的照片完好无损,旁边还有诗句:“我是夜晚温柔闪烁的星星。请不要站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儿,我没有死去。”
奇克的妹妹,德布拉·伯林盖姆成为非常大胆直言的保守主义活动家、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9·11家庭支持美国安全强大”组织的创立人之一。这个组织的使命是:“我们支持美国军方,赞同主动出击原则, 9·11委员会关于恐怖主义威胁的声明支持我们的立场:‘如果危险已经发生,显然那时动员人们行动要容易得多—但可能已经太迟了。’”
德布拉·伯林盖姆大力反对在离归零地两个街区的地方建一座穆斯林文化中心和清真寺。修建计划于2011年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内有五十套公寓的四十三层公寓楼和一座三层的伊斯兰博物馆,没有清真寺。
4
“我们永远在寻找着下一次威胁,
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凯文·纳西帕尼少校9月11日临近半夜才离开纽约州罗马市的东北防空区军营。第四架飞机坠毁已经过去了十三个多小时。天上已经没有民用飞机了。但是,纳西帕尼离开作战行动楼层的时候,还在等着“另一只鞋”掉下来:来自海外的更多劫机行动。
尽管非常疲倦,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不断地苦思冥想,分门别类:他和部下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不对。纳西帕尼认为,在美国劫机的计划中有“估计不止”四架飞机,但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本·斯利尼的禁飞令阻止了其他阴谋。那天晚上,他不可能睡觉了。纳西帕尼知道,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意味着他的工作日会更长。他走进自己装修了一半的厕所,心里想:“这下子谁来干这个啊?”
随后一年中,纳西帕尼和部下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工作六天,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观察着下一轮袭击,但它从未出现。后来,当他因为在9·11那天处理各种信息和通讯方面的工作获得赞扬和嘉奖时,纳西帕尼开玩笑说,这是他在餐桌上听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互相交叉谈话锻炼出来的本事。
尽管预算和人员都有增加,有强有力的技术侦察天空,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军方也建立了新的通讯渠道,纳西帕尼还是十分戒备。“我们集中在内部和外部,永远在寻找着下一次威胁,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2014年退休前不久他这样说,“我的意思是,你听那些电视上的主持人们说,‘哦,这事不会再发生了,不会再发生了’……嗯,但是你看,它确实发生过。所以,我们特别警觉,特别警觉。”
纳西帕尼谈到93号航班上的乘客时特别动感情。“他们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他说,“他们基本上就是做了从长远来讲我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不能让另外一架飞机—我绝对不能让另外一架飞机飞到华盛顿去。”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 来源: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官方网站,摄影JIN S. LEE
5
“从前的伊莱恩在9·11那一天死去了”
伊莱恩·杜克—被严重烧伤的航港局高级行政助理—很快就从圣文森特医院转移到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威尔·康奈尔烧伤中心。她9月11日晚上入院时情况严重,处于药物性昏迷中,有严重的肺部损伤,身体百分之七十七的部位烧伤,生存的可能性很小。
伊莱恩用了几个星期的呼吸机,9月18日至12月11日做了七次皮肤移植手术,还要一次次和肺炎及血液中的细菌做斗争,医生担心肺炎和细菌会要了她的命。她的双胞胎妹妹珍妮特和她们的姐姐玛丽安日夜守护着她。
三个半月后,12月29日,伊莱恩恢复了知觉。她马上想起了她在9·11那天的行动。“你得告诉珍妮特,”她告诉一名护士,“你得保证珍妮特平安无事。”听说伊莱恩醒过来了,珍妮特跟她男朋友说:“我得到了我的圣诞节奇迹。”
一直用了几个星期,伊莱恩才慢慢知道发生的全部故事。尽管有亲身经历,伊莱恩·杜克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听说9·11那些可怕细节的美国成年人。让她接受双子塔不再存在、那么多生命丧失了的事实,可能要花更长时间。
伊莱恩醒过来之后一个月,2002年1月底,她成为最后一个从威尔烧伤中心出院的9·11病人。记者和摄影师们播报过太多讣告,迫切需要与袭击有关的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点关联的好消息,他们蜂拥来到纪念伊莱恩出院的记者招待会。伊莱恩被绷带包得严严实实,坐在轮椅上,她活泼地用一句“嗨,大家好!”来欢迎媒体。她感谢了医生、护士和医院员工,宣布她已经可以去大西洋城光顾她最喜欢的赌场了。至于长期计划,她宣布:“我要回到我从前的样子。”
接下来四个半月,伊莱恩在一家康复中心重新学习如何站立、行走、使用双手及生活。她最后重新学习的技能是如何走楼梯。2002年6月5日,她终于回到位于新泽西州贝永市的家中。航港局的朋友来访时,她经常问起那个她在八十八层要见的信差,但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的命运。过了十六年,她才知道他名叫瓦斯瓦尔德·乔治·霍尔,火球将她烧伤,却将他烧死。她经受了更多的手术和全面的身体康复。“是去地狱里走了十遭。”她说。她的情况有所改善,但身体也只能恢复那么多了。
一年一年过去,伊莱恩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永远不可能不带着痛苦和伤疤生活,不可能完全重新独立,不可能回去工作,也再也不能开车了。她的个性也变了。从前,她是双胞胎里更有自信、能拿主意的那一个,9·11以后她变得胆怯了,那些角色落到了珍妮特身上。伊莱恩甚至对咖啡也没了胃口,在火球吞噬她之前,她最后喝的就是咖啡。她经常说:“从前的伊莱恩在9·11那一天死去了。”
6
“那么多好人,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
9月11日,布赖恩·克拉克和斯坦·普雷姆纳斯的家人都觉得他俩肯定死了。从他俩从三十一层打来电话,到南塔倒塌,中间只隔了二十五分钟。11点15分,南塔倒塌一个多小时以后,布赖恩从轮渡港打来电话,他的妻子黛安娜昏过去了。斯坦看见他的妻子珍妮在门前的阳台上搂着女儿们。他浑身是血和污秽,朝着她们冲过去,结果小女儿没认出他来,躲闪开了。
布赖恩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给斯坦家打了电话留言。看完医生以后,斯坦回了电话,此时已经是9月12日凌晨1点,9·11已经进入历史一个小时了。两个人都认为是对方救了自己的命。后来,他们出现在电视节目和纪念仪式中,但是,他们之间私下度过的时光更为珍贵。布赖恩和黛安娜家的大女儿结婚时,斯坦和珍妮坐在克拉克家人的桌子上,斯坦和珍妮家的大女儿结婚时,也给克拉克夫妇同样的礼遇。布赖恩向客人介绍斯坦时,称他是“我唯一的兄弟”。
9·11以后,统计发现共有十八个人从南塔的七十八层或以上楼层逃脱,他们都走了A楼梯间,至少有一部分路程是在A楼梯间。布赖恩和斯坦是从空中大厅以上生还的四个人之中的两位。第三位是欧洲经纪公司的电讯经理理查德·弗恩,他进了一家理发店,在对讲机里听到朋友们在高层求救时那令人肝肠寸断的声音。第四位是布赖恩的朋友罗恩·迪弗朗切斯科,他最初和布赖恩一起在八十一层搜寻。被浓烟包围后,罗恩追上了那些帮助那个体形壮实的女士的人。罗恩告诉记者,他觉得他爬到了九十一层,然后又下来。他在大楼倒塌前一瞬间逃了出来,不过头部受了重伤,身体上的烧伤面积有百分之六十。
斯坦的伤很快就恢复了。他和布赖恩的关系多少减轻了他作为幸存者的内疚。斯坦因为让临时工德利斯·索里亚诺回家而略觉安慰,但大楼倒塌时,那些听说南塔是安全的,便又和他一起回来上班的同事和朋友都死了。他们中有约翰·“杰克”· 安德烈亚基奥、曼尼·戈麦斯、川内秀也、阿丽莎·莱文、约瑟夫·祖卡拉、布赖恩·汤普森,他在电梯里还和布赖恩·汤普森开过玩笑:“你最好开始考虑另谋高就。”
斯坦回去上班了,但很多年都一直做噩梦。他不断地纠结一个问题:“那么多好人,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他更深地钻入信仰,学会接纳现实,然后开始说:“为什么不能是我?”斯坦经常在教会发言,通过圣经教义讲述他生还的故事。“生活,”他说,“就是站起来往前走。”
但是,斯坦的一部分还是留在了已成幻影的南塔里。他保留着那双把他带到安全地带的满是灰尘的鞋,鞋跟里嵌着玻璃碴子,他把鞋装在一只标有“拯救”的盒子里。斯坦也保留着布赖恩的手电筒,后来他们把它捐献给了纽约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
9·11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布赖恩在教堂讲述他的故事时,第一次流泪了。欧洲经纪公司失去了六十一名员工,包括博比·科尔、戴夫·维拉、凯文·约克和其他帮助那个体形壮实的女士和瘦弱男子上楼的人。同时遇难的还有苏珊·波利奥和兰迪·斯科特,兰迪从八十四层扔下了那张悲惨的条子。2011年8月,十年之后,兰迪的妻子才听说这条消息,纸条上面血指印的DNA匹配上了。
9·11之后一周,布赖恩梦见了何塞·马雷罗,他俩曾在六十八层的楼梯间里相遇,在大楼倒塌时何塞没能逃生。在梦中,何塞穿着白衬衣,笑容灿烂。“何塞,你还活着!”布赖恩大叫,“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布赖恩没有听见回音。这个梦没有减轻他的忧伤,但至少让他感到平静。
2006年退休之前,布赖恩帮助重建欧洲经纪公司,并且管理一笔救济基金,给公司丧生员工的家属发放了五百多万美元。
布赖恩和斯坦在失落中生活着,但是,他们珍惜一项收获。从他们第一次相见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他们仍然认为对方是自己的血肉兄弟。

《9·11:美国心脏》剧照
7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
为身为一名消防队员而感到自豪。”
消防队长杰伊·乔纳斯和第六云梯消防队的消防员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没有在B楼梯间里碰到约瑟芬·哈里斯,他们很可能就死了。
如果他们坚持原来一步两阶的疏散计划,他们可能会在大堂里追上消防大队长理查德·普朗蒂,而普朗蒂就是在大堂里死的。如果他们跑得更快,可能正好出了北塔,倒下的北塔砸死了消防局长小彼得·甘奇、第一文职副局长威廉·菲恩,还有很多其他人。或者,如果他们像其他消防队员那样留在后面,如果杰伊没有在南塔倒塌时马上命令他们撤退,第六云梯消防队也可能会在塔里更高的楼层,没有时间营救自己或者约瑟芬。
漫长的夜晚,杰伊会回想起朋友们的面孔,重播9·11那天他在一堆废料旁边和另一名消防队长的对话。“祝贺!”吉姆·里奇斯告诉杰伊,“我听见你所有的广播对话了。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听到最戏剧化的事了。顺便问一下,你看见第四泵浦车消防队了吗?”吉姆·里奇斯是在找他的大儿子,消防队员吉米·里奇斯。杰伊没看见他。
那些想法是后来才有的。9·11那天下午,他首先必须回家。北塔倒塌,砸坏了第六云梯消防队的消防车,他只能靠那双疲惫的双腿走回家。杰伊把头盔扶正,抓上撬棒,向北沿街走去,街上满是从粉碎的大楼里飘出的碎粉,没有车,也没有人。
杰伊进了唐人街,沿着坚尼街的马路中间往前走着,任何别的日子,这么走路必死无疑。他觉得自己像卡通人物猪圈仔乒乓*一样,污秽黏附在他的皮肤上,走路时,后面飘着一阵灰尘的烟雾。杰伊觉得路人都在看他,于是转过身来,看见大约二十个华人保持着礼貌的距离,跟随着他。
一个人追上杰伊的脚步。“你没事吧?”他问。
“没事,”杰伊说,“只要我坚持走着就没事。我要是停下来,可就再也不想重新开始了。”
“你去哪儿?”
“坚尼街和艾伦街路口那个消防站。”
“好吧,”那个人说,“我们护送你走到那儿。”
这些华人像庄严的荣誉卫士一样护送杰伊走完了通往第六云梯消防队消防站的剩余路段。他在那里给哭泣着的妻子朱迪打了电话,告诉她,他是多么爱她和他们的孩子。
人们以千百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对纽约消防队员、航港局和纽约警察局成员及其他应急反应人员表达敬意,这些华人护卫着杰伊,只是其中一个实例。后面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在葬礼和眼泪中,全国上下对他们表达了源源不断的感激之情。
遇难者中有三百四十三名消防队员和医护人员。死伤人数,远远超过了纽约消防局历史上最坏的一天:1966年,在曼哈顿一座褐砂石房子的火灾中牺牲了十二名消防队员。9·11那天牺牲的,包括杰伊那天要么面对面、要么通过对讲机联系过的十几个朋友和同事:理查德·普朗蒂大队长;消防队长帕迪·布朗、比利·伯克和特里·哈顿,哈顿死时还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怀孕;消防小队长彼得·弗罗因德、丹尼斯·莫伊察和迈克尔·沃霍拉;消防队员福斯蒂诺·阿波斯托尔、安德鲁·弗雷德里克斯、斯科特·科佩特科、肯尼思·马里诺、格里·内文斯、道格·厄尔什莱格和戴夫·韦斯。
死者中还有消防小队长威廉·“比利”·麦克吉恩,他从前在第十一云梯消防队时是杰伊的部下,是他马上就警告“这可能是恐怖主义袭击”。消防大队长约瑟夫·普法伊费尔的弟弟凯文·普法伊费尔在北塔倒塌时丧生。纽约消防局一年一度的健身奖改为以消防大队长奥里奥·帕尔默的名字命名,在奥里奥带人走上南塔之前,杰伊在北塔的大堂见过他。
消防队员詹姆斯·里奇斯也死了,搜寻人员在曾经是北塔大堂的地方发现了他。“大吉米”和三个小儿子把国旗遮盖下的“小吉米”的遗骸从归零地扛出来。后来,剩下的三个里奇斯兄弟全部加入纽约消防局,就像他们的父亲和长兄一样。
死亡名单上还包括三十七名航港局警察,其中有局长费迪南德·“弗雷德”· 莫罗内,塞西莉亚·利洛在楼梯间里碰见过他;还有纽约警察局的二十三名警察;私人医疗公司的八名医护人员;纽约消防巡逻队的一名成员。另外,还有戴维·利姆的搭档,一只能嗅出炸弹的拉布拉多犬:天狼星。
在悲痛之中,也流传着后来成为“B楼梯间奇迹”的故事。NBC的制片人让第六云梯消防队的成员和约瑟芬·哈里斯在《日界线》重逢了。镜头下,他们认为是她让他们生还,而她则对他们满口称赞。“他们是我碰见过的(最)坚强、勇敢、体贴、善良的人,”约瑟芬说,“我害怕时,他们握住我的手。我冷的时候,他们脱下自己的外套,给我披上。他们告诉我不要害怕,他们会把我带出来。他们真把我带出来了。他们太优秀了。”
约瑟芬成了第六云梯消防队的荣誉成员,他们给了她一个比大队长还高的级别。她的制服上印着“守护天使”。
随后的几年,他们的友谊延续下来。萨尔·达戈斯蒂诺邀请约瑟芬参加了他的婚礼。杰伊和其他队员邀请她一同参加媒体访谈、9·11纪念活动和游行等。其中一次,她像皇室一样从敞篷车里向外招手,而他们则随车走着,是她披挂整齐的宫廷侍卫。
尽管搬到了新的消防站,尽管提拔和退休把第六云梯消防队的人送往不同的方向,他们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紧密。不过,虽然约瑟芬乐于和他们联系,她仍然非常私密,不让他们知道她经济上的困难和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杰伊希望约瑟芬能够参加9·11十周年的活动,在媒体上露面,但2011年1月,她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故去,很显然是心脏病发作。
约瑟芬·哈里斯去世时六十九岁。她的葬礼是由退休的纽约大主教爱德华·伊根红衣主教主持的,还有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等人参加。她被装在一副蓝色的钢棺里安葬,丝绒的里衬上绣着消防队员和天使手拉手前进的图案。杰伊和第六云梯消防队的队员们作为抬棺人,最后一次抬起约瑟芬。
许多年过去了,杰伊还是时常有幸存者的内疚感,他还忍受着肺部的损伤。但是,他继续受到提拔,从消防大队长提升到副局长,主管纽约消防局在布朗克斯和曼哈顿上城的消防分队。他从很多方面得到乐趣:供养家庭、领导团队、出版一份关于训练和安全的月刊,用纽约历史上的火灾教授经验教训和技术。他经常描述9·11时死在他身边的人的英雄行为。
杰伊也到了接近退休的年纪了,一个秋天的下午,他坐在布鲁克林一家消防站里,这家消防站的红门上画着两名天使跪在一个弯着腰的消防队员身旁的图案。图案上面用华丽的字体雕刻着“2001年9月11日,天使哭泣的那一天”。杰伊倒上一杯黑咖啡,关上办公室的门,重新提起了9·11。他谈到第六云梯消防队如何爬上北塔的B楼梯间,他们如何救了约瑟芬,约瑟芬如何救了他们,还有多少无辜、勇敢的人死在了那些蓄意杀人的狂热分子手里。
一个情景接一个情景,一级又一级台阶,杰伊讲述着“铁人”比利·巴特勒、“房顶哥”萨尔·达戈斯蒂诺、“罐哥”汤米·法尔科、“拖拉哥”马特·科莫罗夫斯基、“的哥”迈克·梅尔德伦,还有他自己—杰伊·乔纳斯消防队长等英雄们的故事。几个小时过去了,夜幕降临。故事结束时,杰伊靠在椅子上,柔声说:“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为身为一名消防队员而感到自豪。”
摘编 | 刘亚光
编辑 | 宫照华
校对 |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