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沙日出生命运如何的简单介绍
一凡

布须曼少女在向人们展示传统药材 徐薇摄于2011年
1914年10月13日,劳伦斯·凡·德·普斯特8岁,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立下志愿,等我长大,我要到卡拉哈里沙漠去寻找布须曼人。”
生活在南非的他,从小浸润在和布须曼人有关的故事和传说中,他的奶妈就是布须曼人。

劳伦斯·凡·德·普斯特,作家、探险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1906年生于南非联邦,1950年代开始探索非洲并以之为创作题材,1981年荣获大不列颠帝国骑士勋章。
年幼时,他对这支部族的命运充满同情:“一切都对这些小猎人不利,而我总是同情这些不屈不挠的反抗者,尽管似乎连上天乃至生命本身都背弃了他们。”
遥远北方的黑人族群大举南下,侵入布须曼人的地盘,并且进一步沿着东西海岸和非洲中部向内深入其古老土地的心脏地带时,白人则从南部好望角登陆,从后方拦截他们。自那时起,布须曼人就面临一场从四面八方全面入侵的战争。
“他们没有要求宽赦,也没有人放他们一马。他们只是孤单地奋起反抗,带着满满的箭袋,再将另一袋用头带系着,然后灵巧地拉弓向敌人射去。”
普斯特带着悲悯和崇敬的笔调记取这支族群的历史,他认为,“无论种族为黑或白,都可以借此反省我们全体对非洲第一支矮小民族所施加的恶行,从此展开一段疗程。”
二十多岁时,他曾两次试图进入卡拉哈里沙漠寻找布须曼人,但都因“缺乏足够充沛的精力和足够丰富的想象力而未能达成。”
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普斯特1942年成了日军战俘,直到日本投降。布须曼人似乎始终和他同在,时刻准备挽救他的心智。在战俘营里,日军恐吓他第二天要被处死的当晚,他梦见一个布须曼小女孩的母亲跪在三只眼睛般的布须曼泉水边,头发下垂落至膝盖处,仿佛一束光之瀑布。在她对面,是曾在他家做仆人的一位布须曼小老头,孩子模样。他们一起将手伸入水中,掬起一捧清澈的泉水向他伸来。普斯特的母亲则微笑着说:“这是开始。”
醒来时,他清楚地感到自己会继续活下去,“心中也明白,环绕着小布须曼人的整个失落的世界又再度和我有了联系,而且依旧完整、鲜明,仿佛这期间并没有任何长年忽视的存在。”
普斯特一度认为自己没有学术背景,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寻找布须曼人并记录他们文化的人,直到1955年才真正下定决心。也正是这个决心,为他打开了许多机遇,让他踏出旅途第一步。
之后,普斯特顺利获得BBC的支持,拍摄一部这次探险的纪录片。他找来两位志同道合且沙漠经验老到的朋友同行。其中之一本·哈瑟拉尔尽管是欧洲人,但在卡拉哈里西部的一个小绿洲出生长大,一家人都曾获得布须曼人的帮助,他的保姆和玩伴也都是布须曼人,所以他会说布须曼语,也了解布须曼人和他们有关沙漠生活的独特知识。哈瑟拉尔的生活经历帮了大忙。
他们计划在雨季来临前最难熬的旱季深入沙漠,因为只有在那时,仍选择坚持在沙漠里生活的才是真正的布须曼人。探险队从卡拉哈里北部边境展开旅程,深入内陆,来到昏睡病猖獗的沼泽阻隔地带,沿着沼泽边缘去寻找传说中的布须曼部族分支——河流布须曼人。
这段艰苦、恼人、充满焦虑的旅程并没有给普斯特多大的回报,他甚至在找到一小群河流布须曼人后有种“奇怪的上当感”。

当代布须曼人展演他们文化的营地 徐薇摄于2011年
在一个几乎有些残破的布须曼人营地里,只有几位妇女和孩子,男人们都去沼泽边缘卖皮毛了,且归期未定。这些人尽管保持着和沼泽相连的生活方式,但却无法展现更多精神内涵。
不过,在帮助普斯特深入沼泽的船夫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先知巫医萨木丘叟,他和探险家发展出了彼此信赖的情谊。他告诉普斯特,自己见过真正的布须曼人,但不是在沼地,而是“从沼泽中他所住的地方走个几天,会进入一片有几座孤零零小山的沙漠里。布须曼人称那些小山为措迪洛山,认为那儿是非常古老、非常重要的神明居处。”
这位船夫向普斯特描绘自己见到过的盛况:“夜晚,这些神灵从祂们的房间出来,去巡视依祂们而造的生物。祂们夜巡时所留下的踪迹、蹄印,至今仍深印在措迪洛山的岩壁上。在中央山丘的一个地方,住着众神之神。在那下面,有一池深水,从来没有干涸过。池水旁边长着一棵树,结着真知果。树旁坚硬的岩石便是众神之神在创造世界的那一天跪在上面祈祷的石块。岩石上的凹陷便是祂当时摆放盛圣水容器的地方,而祂跪下祈祷并创造世界时所留的膝盖印记,至今依然可见。四周光滑的岩壁上绘满了这位伟大神灵所创造的动物,而所有的岩壁缝都住着大群蜜蜂,它们喝永不干涸的池中水,钻入沙漠花朵中吸取花蜜,为神灵们制造最甜美的蜂蜜。在那儿,他说,每年一次,布须曼人会前来相聚一段短短的时间。”
普斯特被他的描述深深打动,并请他带路前去一探。萨木丘叟提出两个要求。首先,必须解决探险队的内部矛盾,第二,不论发生什么,在前往圣地的旅途中都不能打猎杀生,为了食物或是遭到攻击都不行。不然,他们很可能被那儿的神明处死。

沙漠里的小西瓜是布须曼人的主要水源 徐薇摄于2011年

布须曼人的传统窝棚 徐薇摄于2011年
普斯特答应了,但探险过程中碰到的各种糟心事,让他忘记告诫同伴们不能打猎——直到他和萨木丘叟听到枪响。
这为普斯特第二段探寻之旅蒙上了阴影。他们不断经历诡异的磨难,每天早上遭受蜜蜂疯狂的攻击、摄像师的机器不断卡片最后坏了,不得不拿出沙漠花很长时间修理。
普斯特找到布须曼人精美的岩画,还有一处小小营地,而且“显然是最近才有布须曼人扎过营的地方。那儿有一些为遮蔽日光和雨露而用草和刺槐枝叶搭成的轻巧网架,四周的沙上布满了有些已经破损的空贝壳,还有枯萎的瓜皮、野兔毛皮、豪猪的硬毛、乌龟壳和动物的蹄;也有一些新鲜的长颈鹿胫骨,上面不存一丝肉和肌腱以及布须曼人最爱的骨髓。
此外,那儿仍保留着布须曼人生火后的余烬,以及一个用肌腱缝制的破损皮囊——布须曼猎人将这种皮囊背在肩上,上面装饰着用鸵鸟蛋壳制作的珠饰;还有一个破损的布须曼四弦琴。”他们一个星期前才离开,要到下一个冬天才会回到这里。

布须曼老人在钻木取火 徐薇摄于2011年
最终,普斯特真切地写了一封给神明的道歉信,埋到神圣岩画下,然后请萨木丘叟占卜,神明是否原谅的他们。得到的答案是:“没事了,主人。神灵要我告诉你,之后一切将很顺利。祂们只警告我,当你抵达下一个地点时,你会发现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在等着你,祂们请你不要灰心丧气,因为那是属于过去的不愉快,而非未来。”
磨难也确实接近尽头。普斯特的第三趟尝试更像是真正的随心而走。
哈瑟拉尔说他记忆里不断出现一个画面,是一支小小的纯种布须曼人族群,聚居在某些“啜井”(sip-wells)一带。他和他的父亲有一次轻率地穿过沙漠,差点儿没命,却意外闯进那里。虽然当时他只是个孩子,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条路径,他感觉可以凭着记忆再次找到那个地方。
就这样,他们在当地雇佣了一位在农庄工作,但依然和自己的族群文化相连的布须曼人达布,一起沿着哈瑟拉尔的记忆深入沙漠。奇迹发生了。
他们遇见了真正的布须曼人,达布以传统方式向他打招呼:“你好!我从远处就看见你了,我快饿死了。”这个年轻的布须曼人把矛往沙里一插,举起右手,五指伸直向上,害羞地走来,答:“你好!我本来已经死了,但现在你来了,我又活了。”
这个名叫恩修的布须曼人,“全身赤裸,只在腰间围了块小羚羊皮制的胯布;皮肤是新鲜杏实的黄色,有些地方还沾着刚刚宰杀的一头动物的鲜血。总而言之,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野性美,甚至他的气味都充满了野性大地和野生动物的气息,闻起来很古老,也很呛人,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神秘。”

老人手举的植物既是传统药材,也是一种染料 徐薇摄于2011年
恩修这个名字是“盛食物的木碗”之意。他既是个出色的猎人,同时也是为族人提供精神食粮的音乐家。
恩修带探险队前往他们营地的第一个早上,普斯特“借着火光洗脸时,听到远处的狮吼像流星般逐渐消逝,这时突然响起一个新的声音。黑暗中位于我们和天空中第一道曙光之间的某处矮树丛中传来音乐声。乐音抑扬顿挫,越来越大声,是旅行者怀乡的曲调,带着离别的忧伤,却又有旅程中自由昂扬的欢乐。”
很快,披着一件皮斗篷的恩修出现在火光中,“一边走一边低头弹奏着某种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乐器的形状像一把长弓,弓上只有一根弦,从中间向后绑。乐器一端在他的嘴里,另一端在他的左手上,他用一根小木条在两边拨动绷紧的琴弦,用嘴控制反响,奏出美妙的音符。”
后来,他们常常听到恩修演奏。和布须曼人一起去打猎时,有一天,“天还未亮,我刚醒来,惊奇地发现星星从沙漠边缘一颗一颗升上来,景色清晰而壮观。我看过无数次日升月落,但即使是在海上,也从来没看到过星星升起。就在那时,恩修突然开始弹奏他那如泉水般滔滔不绝的旅行曲调。那曲调和声音,以及远方星子跃动的星光,还有无尽黑暗的波动起伏,在银河的岩石上碎裂成泡沫向外喷溅,一切都融合得如此完美,令我感动得如同第一次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那饱满的人声合唱无惧地上升至最后,决心要从那小我的悲剧命运中找到普世界真理的一刻。”
普斯特发现,对布须曼人来说,音乐就和水、食物和火一样重要。“因为我们从没发现任何一支穷困或绝望到没有任何乐器的布须曼族群。而且他们所有的旋律、歌词、节奏等,全在他们的舞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布须曼人不再绘画了,“当我问起他们有关绘画的事情时,他们脸色一暗,并摇摇头。我有一些美丽的布须曼绘画复制品,是无私的斯托在我的家乡自由邦复制的。当我拿出这些复制品给他们看时,年纪最大的那对老夫妇开始哭起来,把头埋在臂弯里,好像他们的心都碎了。”

广阔的南部非洲稀树草原,不远处的阴影是正在下着的雨 徐薇摄于2011年
普斯特观察着布须曼人和沙漠深刻相连的方方面面。
“我经常在正午时分看见恩修和他的同伴在我们身旁的淡淡阴影中倒下,立刻睡着。那阴影其实只不过是光线稍暗淡的一个模糊轮廓罢了。与其说他们是因长距离奔跑而疲累,倒不如说是因天气太热而虚脱。这可能是他们所有生活场景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因为他们对这贫瘠的沙漠大地投以毫无保留的信任,而这对我们来说无法忍受的沙漠,事实上也用它原始的方式慈蔼地回应着他们。他们舒适地贴着地面,在大地温暖的怀抱里睡得香甜。但等他们一醒来,便立刻站起身,仔细观察天空是否有任何云朵或下雨的迹象,好像在他们香沉的梦中,他们也听见大地之母喊着:‘亲爱的老天爷,难道干旱还不结束吗?‘”
布须曼人分享经验、生活、艺术,但他们一直不和普斯特分享精神内涵,普斯特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除非那人已经接受过舞蹈的神秘洗礼。”
要跳舞,就要举行仪式,最好的理由,就是猎取一头大羚羊。普斯特流畅、饱含细节地描述他们和布须曼人一起,展开宏大的大羚羊狩猎之旅。在振奋人心的字里行间,旅途的漫长、疲惫、两趟探寻的失败、累积的压抑统统得到释放。
之后,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艰难的旱季结束了,雨季来临,告别的时候也到了。布须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都安静地躲开,“只有恩修试图唱着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旅人之歌。”
离别总是很难。普斯特记下同伴说的话:“一名北方的老猎人有回告诉我,无论你在哪个地方的灌木林里扎过营,你就留下了自己的一部分在那里。我对这里的感觉正是如此,而且更甚于其他地方。”
当他驾车离开,开到营地后的沙丘顶端,停下来跨出车门向外回望时,“我们的旧营地里已没有升起的烟,也没有任何人影或有人居住过的迹象。那里的沙漠看起来一成不变的空旷。然而在闪亮的尖叶之后、无尽的红沙所带来的奇迹以及雨水滋润后长出的花朵和荆棘组构的浩瀚世界中,我内心的孩童开始和外表这个大人合二为一。沙漠不可能再是虚空的了,因为在那儿,我那颗属于布须曼人的心灵现在有了活生生的亲人和家园得以依归。”他的人生之旅终于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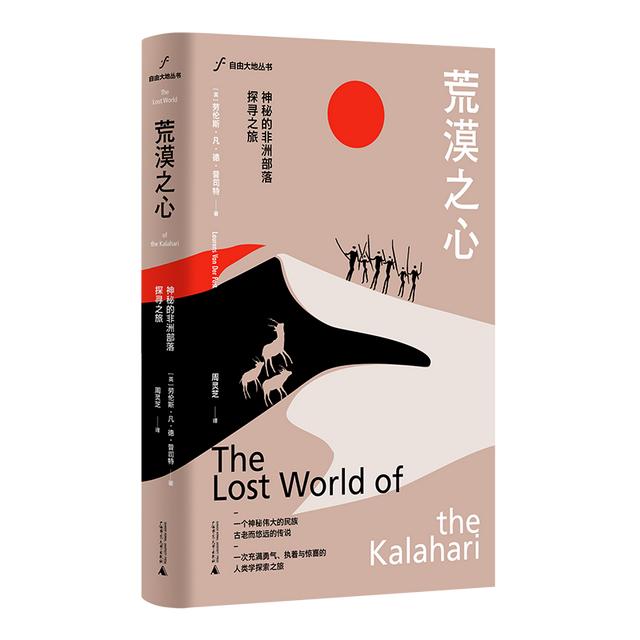
《荒漠之心——神秘的非洲部落探寻之旅》;[英] 劳伦斯·凡·德·普司特;自由大地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责任编辑:徐颖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