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如何变化
随着电脑网络技术与智能化的发展,公司和组织可以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大幅度削减开支,同时缩小公司规模或者将多家公司合并经营。尤其是疫情全球大流行下,金融和经济深受影响乃至衰退,公司和组织一定是成本最优化、风险最小化以及生存目标化。在这样情况下,中等收入工作市场就注定萎缩,并且成为必然的趋势。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疫情作为“外部性”加速了彼此之间的割裂乃至断裂,战后所建构的经济繁荣史是靠技术革新和社会财富的广泛提高与彼此连接而成的,但如今这种利好不再存在——早在前几年这种趋势就已经开始了,而全球疫情则加速了这一趋势。于是,尽管技术创新依然能为整个社会带来财富,但财富会加剧流向了极少数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某些行业和社会阶层的人被完全排除在财富的分配之外”。因此,世界会加速两级分化。
赢家通吃是必然的,而且越来越厉害,中小型企业会受到碾压,创富的机会越来越少,试错成本越来越高,一不小心就会返贫。
科技发展的确创造了财富,但大多数人并不能或很难再从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未来社会是两极化的,中间层消减乃至衰亡。
此外,如今的创新变得更加的难,不再像战后的几十年的那样迅捷和快速。技术创新的红利池不再像想象的那样巨大——即使有较大的红利池,它首先也是属于极少数人的。
就像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曾经说的,“那些挂在较低树枝上的水果”早已被我们摘下吃掉了。“今天要取得同样具有划时代的突破性创新成果,确实比过去更难,成本也更高。”《冲动的社会》著作者保罗.罗伯茨也如此表示。
 第二大变化:机器人替代人的速度加快,劳动伦理逐渐走向末日。
第二大变化:机器人替代人的速度加快,劳动伦理逐渐走向末日。罗伯茨的另一个思想我是非常认同的:制造业未来的工作岗位将不再是所谓的蓝领岗位,而会变成无领岗位。“被机器人逐渐取代的工作远不止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岗位。”
我们的社会显然已经不再是“生产者”社会——不再是所谓的“劳动文明”——然而,我们又无力创建“空闲时间文明”,结果对劳动、时间和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到了荒谬的地步。我们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微电子革命所开创的新职业及其导致的工业化劳动性质的根本改变上,特别是劳动条件的改变。我们被告知:重复性和纯粹执行性的工作将从工业领域消失,今后工业劳动将逐步变成吸引人、尽责任、自我组织、形式多样的劳动,要求个人具有独立、创新、沟通以及学习掌握跨学科、多样化的脑体力知识的能力。于是,以往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班,将被新的阶层所接过。再进一步的趋势则是:当机器人全部应用到工作场景中去的时候,社会中的人们的全职工作就注定不是必需的,而且失去了经济用途。如此的话,这个社会将何去何从?如何确保人们既有工作而且工作又少又好并且还能得到一份社会财富?…按此趋势进行研判的话,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未来唯一有可能创造大量就业的活动就是仆佣服务——经济“三产化”和以“服务社会”取代“工业社会”。
大家都知道,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实现了“生产替代”——工业的生产和产业化服务取代了家庭的自给自足和个人的自我服务,但如今整个社会正走进“等价替代”的时代,但这个显然是“非生产性的”“仆佣就业”,本质上是没有创造生产和财富增长,只是进行了有限财富的重新转移分配。
长此以往,一个趋势结果就是:劳动伦理的末日。因为,劳动不再是主要的生产力来源,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衡量标准。企业借助电脑程序、大数据、算法等取代人力劳动,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时无限降低雇佣人数——大量的雇员注定消失,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趋于瓦解,之前的所谓“阶级对抗”无法再按传统的范式予以定义。于是,超越阶级界限的运动、变革和横向联盟出现了,更多的人不再被标签和符号成哪个阶级,他或她都成为独特的个体,他们或她们之间,或合作或对抗。
大量的工薪关系会消亡。“非阶级”(或“第四阶级”)会出现。
 第三大变化:社会阶层会重新变化:“超级劳动者”(包括资源与财富的拥有者),服务提供者(技能输出派)以及大量的低技术服务者。其中,社会工作者会形成一种新力量,同时也面临经济挑战。
第三大变化:社会阶层会重新变化:“超级劳动者”(包括资源与财富的拥有者),服务提供者(技能输出派)以及大量的低技术服务者。其中,社会工作者会形成一种新力量,同时也面临经济挑战。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其著作《平均已死》中预测:所有劳动者中最强的前15%将会成为生产力超高的“超级劳动者”,他们不仅非常聪明,而且知道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或者知道如何管理其他的超级生产力要素。因此,对这些超级劳动者而言,每一代新技术的推出都意味着更高的效率,技术的发展能帮助这些超级劳动者获得利润的更大份额。
超级劳动者同时也是资源拥有者和财富掌控者。
超级劳动者之下的第二阶层是少数“服务提供者”——我称之为“技能输出者”,包括按摩师、健身教练、室内装修师、个人助手、课程辅导员、艺术家、心理师、创作者以及其他专业技能输出者。这些人通过向超级劳动者提供服务,获得不菲的报酬。
再之下,就是技术含量相对弱的服务者,基本属于类外包服务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大量的,并且也是最难被取代的,因为他们的很多工作通常需要面对面接触,并提供手工服务。但工资也是较低。
此外,就是不一而足的失业者。这些失业者可能包括了传统的精英、中产以及技能派。
当失业成为常态化会怎样?从终身制全职工作时代到个体化生产劳动时代,个体怎么办?这方面我曾写过专门文章,可以自行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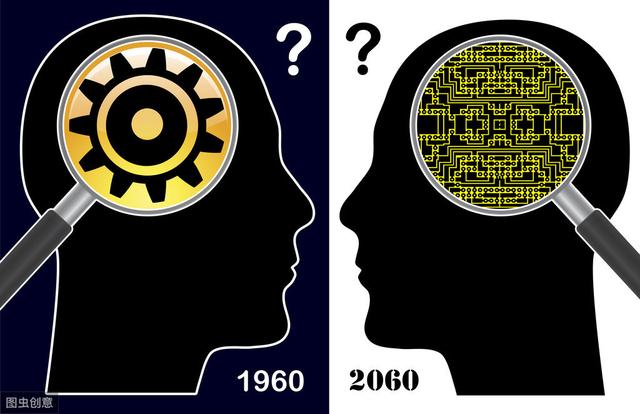 第四大变化:和平与发展遇到挑战,或遭重挫。世界性的集权模式会形成一股力量,新自由主义面临挑战,全球再次处于非常不确定的大变化之中。时代的变化,自然影响个体的命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让历史告诉未来。
第四大变化:和平与发展遇到挑战,或遭重挫。世界性的集权模式会形成一股力量,新自由主义面临挑战,全球再次处于非常不确定的大变化之中。时代的变化,自然影响个体的命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让历史告诉未来。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以及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仇恨”和“不满”的情绪开始四处蔓延。各种对抗的言行开始崛起。其中,德国的希特勒正是这个时候利用如此契机俘获了人心,开启了“乌托邦的实验”,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全球性风险或不一而足的出现,惊涛骇浪般的变化会接二连三。世界的未来,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有着无数的可能性。是好是好,很大程度上决定在政治家们的手里。
危机来了,应对失措。“最可怕的不是危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而是在冲动的社会中,我们面对和处理这些危机的各种能力正在逐渐丧失。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说,由于我们早已习惯了高度个人化的经济模式,我们既不愿意延迟满足,也完全拒绝任何可能让我们脱离舒适区域的事物。然而,更严重的是,曾经帮助我们克服和限制这些个人缺点的公共制度(主要是我们的媒体和政治体系)也已经被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腐蚀而变得极度脆弱,从而丧失了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
我称之为:脆断的世界。
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应对与影响,就可见一斑。“黑天鹅”已发生。
 第五大变化:呼唤与渴望新型互助社区。社会变得更加的陌生,碎片,屏幕化与冲动化……你还快乐吗?它正在摧毁我们的生活…我们敢于反叛吗?
第五大变化:呼唤与渴望新型互助社区。社会变得更加的陌生,碎片,屏幕化与冲动化……你还快乐吗?它正在摧毁我们的生活…我们敢于反叛吗?焦虑,贩卖焦虑;快乐,兜售快乐;…我们处在社会中的“分裂态“中,无法自拔。可怕的是,“我们对冲动的社会的这些反叛行为源自内心的绝望与愤怒,同时也来自信仰的丧失。”
《冲动的社会》一书中的这段话写的特别好:
经济体系正在以极高的效率摧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体系早已被追求高速回报、赢家铜价的短视思维彻底腐蚀,因此收入的不平等、商业界的冷酷与野蛮以及周期性的市场奔溃已经成为社会的新现实。市场失灵现象出现了。“我们不仅看到了效率市场的垮塌,甚至见证了整个市场社会的崩溃。这样的市场社会号称可以鼓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而增加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但市场社会过度鼓励对即时满足的追求,并因此掏空了我们所有的传统价值和生存意义,把我们的主流文化变成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文化。消费者经济不断向我们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却无法真正产出我们需要的东西,这种深刻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宽。”“这些反叛者也许从未对冲动的社会正式宣战,但这些反叛行为随处都在发生,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冲动的社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台无人驾驶的巨型跑步机一样,如果不能让自我与这台机器的惯性、预期和价值观保持适当距离的话,我们会失去某些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东西。”
怎么办?唯有重新连接。如今人们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连接”,希望与他人建立深层次的、真正的、有意义的关系。半个世纪之前,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曾说,人们一直“被对社区的渴望驱动着”。事实上,今天的我们仍然被这种渴望所驱动。
如果说,在冲动的社会的腐蚀下,自我和社区的概念同时出现了垮塌,那么在反抗冲动的社会的运动中,我们必须同时重建自我和社区的功能。
当自我和社区之间存在健康的关系时,自我和社区之间可以赋予彼此更多的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中,社区是健康的社区,而社区的基本价值(共同的目标、合作、风险、耐心以及长期承诺)也能对自我祈祷支撑作用,并赋予自我回馈社区的能力。这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回顾历史,在市场瓦解社区的过程中,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
当远离市场的价值体系,社区的价值体系便能重新回到生活中。即便只是适度远离市场的控制,也能感受到极大的快乐和真实感,这来源于人们与社区重新建立起来的联系。这种快乐和真实感鼓励人们进一步扩大市场和自我的距离,于是人们和社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深入和持久。
将自我和社区重新连接的欲望,就像裂缝中的野草一样蓬勃地生长起来。一方面,这野草会努力向着太阳的方向生长,另一方面,野草的根系则会深深地扎入社会的根基。但社区同时面临着自我成长和自我造血的挑战。所以,需要一场更加新型的社区实验。
这同样属于社会治理体系的范畴,但需要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参与和赋能。

本文为原创,未经许可,严禁私自转载。同时,推荐书单:《冲动的社会》,《风险社会》,《大萧条》,《事实》,《平均已死》。感谢睿智的好书著作者们,向思想生产者们致敬。此外,涉及个体的职业请见文中所列的“技能输出者”:一技之长,愈发重要。